-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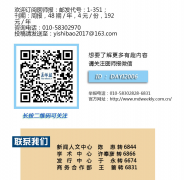
new 并非所有垂体腺瘤都需治疗
在追求个人进步时,既考虑自己,又考虑他人,还考虑整体,这是所有接触过他的人对他最深的印象。他,就是中国垂体腺瘤协作组(以下简称“协作组”)组长、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任直。 为将我国国内从事垂体腺瘤诊疗和研究的同道们团结起来,规范垂体腺瘤诊治行为,普及垂体腺瘤相关知识,开展多中心前瞻性临床研究,提高垂体腺瘤诊治水平,以便更好地为垂体腺瘤患者服务,2012年,在王任直等人的发起组织下,中国垂体腺瘤协作组成立。 王任直介绍,截至目前,协作组已汇集来自神经外科、内分泌科、放射治疗、妇科内分泌、神经影像学、神
2017-09-07 -

new 龚侃:把肿瘤想象成蒲公英
龚侃,人如其名,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北京人,带着“京式”调侃劲儿。他特有的“侃”式问诊,让身边的同事和患者在较为艰辛的医疗过程当中总是能感受到一丝难得的喜感。 他不仅传承了泌尿外科研究所老一辈专家的复杂肿瘤切除术和经尿道电切术,而且在酷爱的科研领域打破了中国遗传性肾癌的沉寂,1998年以来龚侃带领团队研究遗传性肾癌,率先阐明了国人散发性肾癌VHL基因突变特点,并制定了我国的诊治流程及指南,填补了我国遗传性肾癌治疗领域的多项空白。 虽然是北大一院泌尿外科最年轻的教授和博导,但大家都习惯称
2017-09-07 -

new 中国医师奖 打造医师的核心价值体系
第十届中国医师奖颁奖大会即将在北京召开。作为医师行业的最高奖项,历经十年,中国医师奖已经具有超越行业、超越奖项的价值与意义。 颁奖前夕,中国医师协会张雁灵会长接受《医师报》专访,畅谈中国医师奖打造医师核心价值体系的责任与使命。 医师报 :作为医师行业最高奖项,中国医师奖得到了党和政府的认可。您认为中国医师奖备受重视的原因是什么? 张雁灵 :中国医师奖是2003年经原卫生部批准,中国医师协会设立的行业最高奖项,2010年经中共中央、国务院审批同意保留该奖项。奖项的设立,旨在通过表彰奖励在医学领域取得优异成绩
2017-09-01 -

脑胶质瘤:精准治疗的历史机遇
近年来,尤其自2012年中国脑胶质瘤协作组(CGCG)成立后,我国脑胶质瘤临床科研事业取得飞跃性发展:开展中国脑胶质瘤基因组图谱计划、构建国内最大的脑胶质瘤生物样本信息库和基因组学数据库、《CGCG成人弥漫性脑胶质瘤临床指南》发表于国际著名期刊…… “新元素的注入必将促进学科进一步发展。我相信在协会力量的支持下,脑胶质瘤专业的同道们将更加专注脑胶质瘤的研究、教学、治疗与防治等,讲好中国脑胶质瘤的故事!”对于刚刚成立的中国医师协会脑胶质瘤专业委员会的未来,首任主任委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江涛教授信
2017-09-01 -

林桐榆:探索肿瘤的已知与未知
林桐榆是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淋巴瘤首席专家,广州这个包容度极高的城市让他拥有一颗包容的心。多年来,林桐榆秉承共通与协作的理念,与南方各省的肿瘤专家共同发起创办了中国南方肿瘤临床研究协会(CSWOG)。在这个以临床研究为主的协会中,谁都可以提出课题,谁都可以参与,团结协作又互通有无。他创办的POST-ASCO会议也和其他会议不同,开放式的环节,医生接二连三地上台谈自己的想法,一屋子人在那里给这些设想挑毛病、提建议,各抒己见,思想的火花屡屡碰撞,场面专业热烈得让人惊叹。 林桐榆总说,一
2017-08-29 -

韩济生:中国疼痛科走过十年
学术缘起:思考针麻是什么
2017-08-23 -

为了科学,应忘记诺贝尔奖
二十世纪以来,物理学界与医学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很多物理学的成果应用于医学领域,惠及人类。在201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来临之际,峰会合作媒体《医师报》记者特邀一位微电子领域的权威专家——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副主席、国家外国专家局原局长、峰会主席团成员马俊如教授,从近期科学界最热门的话题“天使粒子”马约拉纳费米子(一种费米子,它的反粒子就是它本身)的发现入手,深入剖析科学的驱动力、诺奖得主的品质、科学与技术的区别等精彩话题。 搞纯科学的科学家,为兴趣而科研 记者: 您如何看待
2017-08-23 -

缅怀一代名医吴蔚然教授
吴蔚然教授遗愿 8月8日,我国著名医学家、杰出的外科专家、北京医院名誉院长吴蔚然,走过了96个春秋后离开了他奋斗多年的中央保健工作岗位。8月14日,吴蔚然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举行。 吴蔚然教授早在2014年4月就写下遗愿,提出“当我生命走向终结时,尊重自然规律,请不必再采用插管、透析、起搏器等创伤性治疗以拖延无意义生命。需否行遗体解剖,请医师做主决定,并恳请尽可能不开追悼会,不写生平。” 据悉,吴蔚然教授作为原中央保健委员会委员,中央保健委员会第一、二、三届专家组副组长,在周总理病重期间,他曾守护到最
2017-08-21 -

谦和做人 严格做事
吴院长离我们而去了,他和蔼可亲的面孔好像就在我的眼前。 我在1982年出国留学之前,一直做颌面外科的工作,常到其它手术间看一看其它科室的手术,以便学习。特别是遇到吴院长做手术,我一定去看。 吴院长在手术台上,总是一改平时和蔼可亲的面孔,变得非常严肃。他对术中的解剖结构都用英文,伸手要器械也是用英文,有时器械护士几次递的器械不对,他会发脾气,把器械扔掉,大家都很紧张。但是手术完成后,他又恢复了笑容可掬的面孔,和手术护士有说有笑,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我听说有一次,一个年轻大夫给患者消毒、铺巾,违反了无菌原则,
2017-08-2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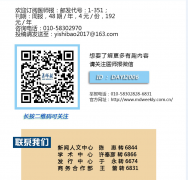
一声“吴大夫”
我是1987年来到北京医院工作的。二十九年前的吴院长比我们现在的年龄也大不了许多,正是承担大量重要工作的年龄,记得当他见到刚来参加工作的我,便问了我的名字,认识了以后每次见了我都叫我“吴大夫”。 当时我刚毕业,同事之间打招呼都很随便,吴院长对我的称呼最正式也对我的心灵最震撼,虽然“大夫”这个称呼在我后来多年工作中被同事和患者或许叫过成百上千次,但这个如此平凡的职业称谓,当时在我看来其实是包含了吴院长那一代医生对自己的同事,无论年资高低的尊重和信任,它激励着一个年轻医生意识到自己的职业,自己的责任和职业的光
2017-08-21

— 医师报官方网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