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真:低调做人 踏实做事
1990年,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医三院)急诊科组建,当时已有的两名医生都是基层医院来三院进修后留在三院工作的,科主任想要一位刚毕业的医生从头培养,主任找到王真,问她愿不愿意干急诊。还没等王真回答,她又问“你怕不怕苦?”“我不怕吃苦”“干急诊会非常苦,而且要求业务能力全面,我看了你在校的成绩单很好,对你非常满意,相信你有潜力,就来急诊工作吧,急诊是一个新的专业,对业务能力的锻炼提高会非常有帮助。”“我不怕吃苦”王真就这样在科主任的“游说”下选择了急诊专业。进入科室后科主任对王真的要求非常严苛:“我对你充满希望,为尽快提高业务,我希望你三年内不要结婚,五年内不要生孩子!”。王真认真遵守了对科主任的承诺。从那天起,她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坚守在高风险、高强度、高难度的急诊一线工作岗位,尽管与她同来或后来的人都离开了,尽管付出和回报极其不相称,她依然无怨无悔的坚守在最繁忙的急诊一线,一干就是3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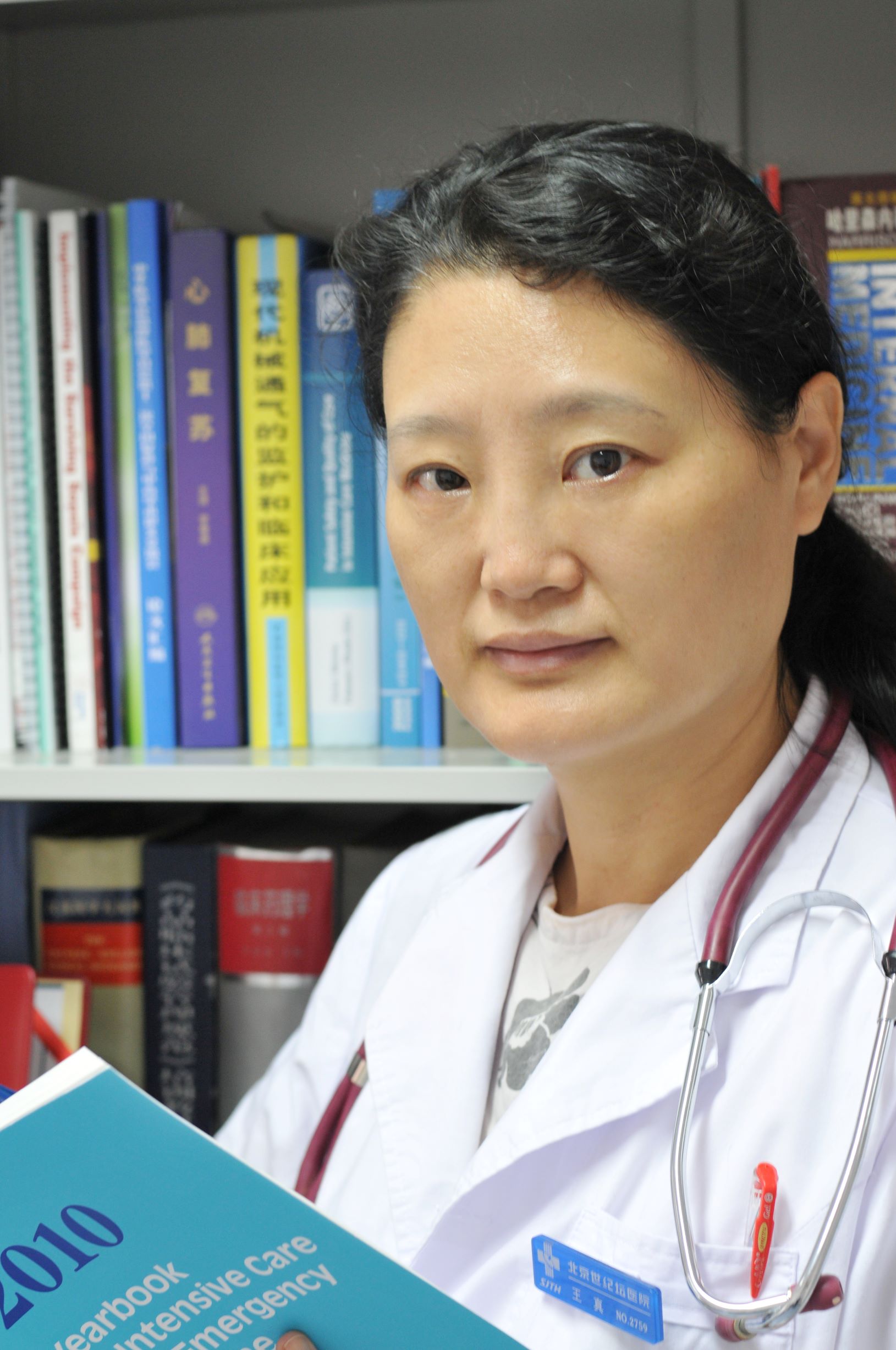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急诊科主任 王真教授
首诊非典患者
2003年4月4日,王真正在北医三院急诊科值二线班,一线值班医生找到她,“有位发热患者来就诊,他说三天前曾接触香港人,香港人也已经发热了。你帮我看一下?”当时“非典型肺炎”(非典)这个名字尚未流行,北京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非典感染患者。只是从3月份开始,王真听说“广州同事在治疗一种特殊的肺炎,患者很快就死掉了,却连病原体是什么都搞不清”。多年的经验让王真警觉起来,王真当机立断——隔离患者!
北医三院急诊科早已人满为患,根本没有单独的隔离室,王真硬是把旁边的一间诊室腾出来。其他患者不明所以,见她给刚来的患者特意安排“单间”,以为是假公济私,便与王真闹了起来。因为患者尚未确诊,王真只能忍着误解与指责解释“他需要自己接受治疗,不让你们进去自然有不能进去的理由。”
经确诊,该患者得的正是非典。由于当时是周末,医院事先也没有准备,临时找来的替班同事因恐惧传染性不愿接触该患者,几天来,王真一直守在隔离诊室观察、治疗该患者。院领导看她一个人太辛苦,再次找人替班。王真索性豁出去了,“我要是被感染的话早就感染了,别再找人来再被感染了。”后来,患者转移至其他医院,王真也被隔离观察——所幸她没有被感染。
然而,非典疫情却开始大面积爆发了。
因为王真在急诊科年资较高,又第一个接诊了非典患者,所以从4月4日到6月份,她作为急诊科主检医师一直待在医院,不仅负责非典隔离病房,还要同时兼管急诊病房(当时全院所有内科病房均已关闭,只有急诊病房还能收治內系病人)。当时天气又热又没有空调,王真天天穿着三级隔离服,很快就全身过敏起了严重荨麻疹。她只好趁没患者的时候静点激素,患者来了再赶紧拔掉点滴看病。那段时间她累得精疲力竭,甚至萌生了“我什么时候也得非典,那样就能休息了”的念头。
王真这么拼命工作,在她看来已经是一种“职业习惯”了。刚做住院医师时,由于科室只有三名医生,她每天16小时守在急诊科,无论周末还是节假日从来没有休息日。彼时急诊科刚成立,还被称为“急诊室”,不仅在医院不受重视、待遇差,工作还特别累。急诊科缺人的时候,其他科室的医生来转科,都说“急诊科的工作量是我们科的五六倍”,没人愿意来。当时医生少、患者多,王真经常忙得顾不上吃饭,以至于落下胃病。甚至她发烧39°多的时候,还得强撑着给发烧38°的患者看病。
用实力征服欧美同行
在临床待的时间越长,继续学习的渴望就越强烈。“临床上有太多问题需要解决了,我应该充实自己,让自己更加符合急诊学科的要求。”于是开始做科研,并又读了北京大学医学部硕士、博士研究生。“那时医生都是疲于奔命地看病,根本没有时间做科研。我都是下了夜班不睡觉去做科研,然后再接着上夜班——就是这么拼出来的!”
2005年,王真凭借出色的临床成绩、科研成果和语言能力,考取了国家留学基金委当年唯一的急诊专业公派留学基金,赴美从事博士后研究,成为美国危重病协会主席Dellinger教授的首位亚洲学生。在美国学习的两年多时间里,王真既从事临床科研,也每天跟着查房,如饥似渴地吸收着先进的急诊与危重症医学知识。起初,王真总是默默无闻,大家既不了解也不重视她,Dellinger教授在向访客介绍他的学生时,她都是最后那个被一带而过的“她是一位中国来的医生”。一年后,当她向课题组汇报自己的研究成果时,Dellinger教授和其他美国同事不禁对她刮目相看,连连称赞她“原来这么棒!,你不爱发表意见以为你不会呢”。后来,Dellinger教授将研究小组的重点全部转向王真,逢人再介绍他的学生时,王真成了第一个被介绍的“这位优雅的女士,是来自中国的非常优秀的教授。”
2011年,王真受法国卫生部邀请,到巴黎Hôtel-Dieu de Paris急救中心做高级访问学者。法国文化和美国文化不同,王真又不矜不伐,起初法国同事对她多少有些傲慢。
有一天,王真跟急救车去抢救一位心脏骤停的患者,经过心外按压气管插管等现场急救后,患者恢复了心跳和呼吸。然而,王真却在现场和急救人员应该把患者送到哪儿继续治疗产生分歧。法国医生认为患者系心脏病突发,应该送往心脏中心救治,而且指南也是这样规定的。而王真认为患者系中毒,应该送往肾脏中心做透析。王真对自己在国内接诊过的大量病例很有信心,甚至敢跟他们打赌。他们先将患者送往心脏中心后患者直接进入导管室,他们就在原地等待,15分钟后心导管检查检查结果出来了——心脏血管没有任何问题。证实了王真的判断。他们又急忙将患者送到肾脏中心,经检查发现患者系“速可眠”中毒。
经过这件事,法国医生对王真的态度发生了很大转变,后来又发现王真在科研方面的成果超过他们时,不免对王真敬佩有加。
在多年国内外的学习、交流经历中,王真笑道“因为我的性格,我不管去哪儿,起初都不会引起关注。最后都是凭实力才获得别人的认可和尊敬。”现在也一样,国内很多急诊同行不了解她,但了解她的人对她的能力又非常钦佩,王真笑说:“我不太适合现在的社会环境”
中国医院急诊发展及现状
作为第一批科班出身的急诊医生,王真从事急诊医学已30年。在这30年间,她深耕于国内急诊临床、科研、管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等领域,并赴美、法深造,还多次受邀在国内外重大急诊医学会议中发言。在她看来,我国的急诊医学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建立之初没有明确的制定学科发展的规划和制度,导致国内医院的急诊科呈自由发展状态。1989年颁布的医院等级评审制度要求成立“独立的急诊科”,所以很多医院只是把原本不独立的急诊科“独立出来了”,然而学科建设、人员培养、制度管理等方面始终没有统一标准。“国外急诊科是在一定框架内发展,而我国急诊科各地模式不同,是自由发展起来的。”王真认为,遑论我国急诊科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是我国内部,基层地区与一二线城市的差距也不容小觑。制定统一的、规范化、标准化的发展规划很重要。
同时,多数大医院急诊科成了很多医院的“院中院”。“我国的急诊科不是典型的急诊科,基本上是‘24小时门诊’。这与现行的医疗体制、社区医疗、养老医疗等各方面发展滞后也不无关系。”例如慢性病患者在家难以得到优质护理,又不符合医院住院部收治要求,他们既想得到治疗,又没有办法,只好挂急诊科。王真在北京市医管局挂职时曾对北京市20余家医院急诊科做过调研,发现急诊患者中“只有不到20%是‘真正的急诊’,超过80%的患者其实看门诊就足够了。”
“因为急诊科不能拒诊,结果患者收治下来,在急诊科住下就不走了”,王真说,滞留在急诊科的患者每年都在增加,在有的医院甚至占急诊科患者的20%~30%,“入口不限制,出口却不通畅,这不就是‘肠梗阻’么。”结果,几乎所有医院的急诊科都在逐年扩大,成了名副其实的“院中院”。
结合多年在国外学术交流的经历,王真认为“中国急诊医生与国外的学术交流还是太少了。”一方面是经费原因,另一方面也受限于科研水平、语言能力。“中国急诊医生的工作量太大,以至于科研成果水平有待提高。”
虽然急诊科仍面临严峻的挑战,但是王真感慨,“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在的急诊科比我们当时好多了。”如今,全国已有10余万名急诊医生,医生在晋升职称时不仅有了急诊专业,申请科研基金时也增设了急诊方向。“以前这些都是没有的,这都是急诊医学发展的成果。”
作为政协委员和最高法院特约监督员,这些年来王真也一直在为营造良好的就医环境,急诊医学的发展及信息化建设等方面进行呼吁,医管局挂职时推动的北京市属医院急诊专项工作并也取得了一些效果。
在急诊科历练了近30年,王真始终是一副平心静气、慢条斯理非常淡定的样子,她说自己的性格就是这样的,“我从不争什么抢什么,别人都说我太低调了。我还是想做点事,不论临床还是科研,或是管理方面,我都希望自己能做得好一些。”
——###——
天普洛安在我国的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出有效性,期待能有大规模的国际临床试验。(王真)
发表评论
最新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