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也是一味“药”
3月1日,中国医师协会第一届医学与文学高峰论坛在龙城常州举行。作为国内首个行业协会搭建的医学与文学跨界对话的平台,本届论坛以“文学也是一味‘药’”为主旨,聚焦医学与文学的关系,呼唤医学人文精神的回归,与会专家们就医学、文学与人文精神的融合等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对话。会上,中国医师协会人文医学专业委员会——医学与文学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会后,《医师报》记者分别专访了医学界与文学界的两位专家,请他们畅谈医学与文学的跨界与交融。
赵美娟:让医学插上文学的翅

“无论科学还是文学,都有自己的坐标,对应着人的生理、心理、智力与精神文化需求、产出与消费,就像每项检测数据反映相应方面的身体健康状况一样,当机体处于动态均衡时,意味着健康,平衡失去时,意味着有问题。”中国医师协会人文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医学院基础教研室主任、医学与文学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赵美娟教授对《医师报》记者说。
科学很有效,但它还不够好
现代医学技术的高速发展让医生对技术顶礼膜拜,甚至出现了技术主义和唯科学至上的倾向。如今,我们已经初尝了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赵美娟说:“如今的医院,往往拼的是量化、标准化、信息化的改造升级,应该说,这些被过度使用了,量化、标准化等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过度量化、标准化,会‘简化’掉丰富性、差异性、异质性,统计学意义上的‘均值’与‘方差’失衡。我们常对患者说,‘来,做个化验吧!’‘去,照个胸片吧!’可是,人在疾病面前的个体差异情况如何掌握?患者的感受性描述、相关叙述是否也是诊疗决策与治疗过程的重要依据与内容?要看到,不仅各种怪病、非典型症状越来越多,而且检测、化验、诊疗的临床指南也存在相对滞后性,看病这件事有那么容易吗?”
医学中,科学无疑是有效的,但仅靠科学却不够。对此,赵美娟说:“人这个复杂有机系统,无法通过器官、组织、细胞的机械地逐层分解来还原完整的人,人在肉体与精神之间以及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决定了单纯机械还原论思维于医学是不够的,而所谓1+1>2的复杂系统论思维与人之生命的不确定、偶然性、复杂性——生命之谜——是契合的。”
对如何看待医学与文学融合的问题,结合此次会议主题,赵美娟表达了看法:“法国著名文学家维克多·雨果说过一句名言:‘科学是我们,艺术是我’,此话可以帮助理解医学与文学融合的意味。科学理性善于抽象、量化、逻辑推理获取“共性”(我们)数据和论证推演的同时,不善于反映个体差异、多元、未知的“个性”(我)的独特内容,诸如用日常语言对疾病症状的独白描述、独特感受、主观经验与渴望的叙说……正是这些经过个体拣选的故事片段,构成了患者独特的心智结构的“自我”,这些不同于科学逻辑语言与思维的关于患者个体差异的‘知识’对诊疗决策、诊疗过程、临床效果都是极为宝贵的。文学性在这里,意味着‘医学是人学’尺度上的进一步扩展;意味着医学对人的整体认识的努力;意味着对医学‘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再度反思与觉悟;意味着对单纯科学逻辑理性方法的矫正。”
诊疗的好坏,最终效果说了算
赵美娟说:“医学为人提供适宜的诊疗与帮助,而诊疗除了依据影像、病理、检验报告以外,患者的感受和意愿等应是临床决策与评估的重要依据。这意味着,诊疗决策过程不像解题那样单纯是学术,因为,逻辑上成立的,实际上未必行的通,就像手术很成功人却死了的道理。医学上的事,最终效果说了算,医生可发挥的余地是有限的,恰当诊疗之‘恰当’二字的意味即在这里。”
赵美娟表示,大多数的患者都不懂医学的专业术语,只会对医生说:我感觉很好/我感觉很糟糕之类的叙事性描述。但在医生的科学规训面前,这样的回答常常是无效的——科学无法定义好与糟糕,科学需要像1+1=2这样的标准答案。而在患者的复杂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面前,单一科学的理性显得有些苍白无力。
人文不是万能的,没有人文,却是万万不能的
同时,赵美娟也清醒地意识到,文学并不是万能的。她说:“我们在强调一个新理念的时候,总是要围绕着这个理念提出很多佐证,从而把这个理念说得如何重要。文学有科学无法取代的作用,但如果把这种作用任意地扩大,我们也同样会走向一个充满了感性与畅想的极端,这不是我们医学要的东西。”
赵美娟表示:我们的初衷不是让医生成为作家,去写小说、创作诗歌;我们只是希望医生能够用文学思维、文学的语言更好地了解患者,了解疾病,进而更加地尊重生命。这才是文学在医学中的价值,才是医学人文精神应有的期许。
梁晓声:要做人文的医生,也要做人文的患者

“我国的医疗资源还很有限,而医生面对的又是世界上最庞大的患者群体,这就很容易使医务人员在繁重的工作中迷失,将救死扶伤的神圣使命简化成缺少人文关怀的机械性行为。而一个没有丝毫人文气息的医院将会是多么可怕的地方啊!”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著名作家梁晓声说。
医生不是神,但医生这个职业却很像神职
梁晓声在谈到自己对医院最初的印象时说:“在我很小的时候,曾经得了很严重的沙眼,两只眼睛都肿了起来。当时,我的父亲正在外地,母亲在上班,没人带我去医院,但我知道医院是治病的地方,于是就懵懵懂懂地一路走去了医院——那是哈尔滨市道里区的一所公安医院,医院不大,离我家大概两站车的距离,但当我走到的时候,医院已经快下班了。”
梁晓声清晰地记得,当时两位穿白大褂的护士正准备下班,见到未带分文的他走进诊室,两位护士二话不说,立刻帮他冲洗了沙眼。“我记得非常清楚——一位护士帮我把眼皮翻开,另一位护士拿着棉签,用一把像长嘴小茶壶一样、装满药水的小壶反复为我冲洗,洗完后还给了我一盒红霉素眼药膏。我回到家,几天后眼睛就好起来了。”梁晓声感慨地说:“这种对医护的感恩之情一直伴随着我的人生。我想如果人间真有天使,那么,他们一定是医生、护士的样子。”
梁晓声表示,医生不是神,但医生这个职业确实很像神职。而从事神职的人,实际上就是最大程度地克服了人性的弱点,形成一种无需提醒的自觉。他说:“每名医生心里大概都有一种神圣感,一种对生命的敬畏感。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去谈文学的思维带给医生的好处。”
做一名有人文精神的患者
梁晓声说:“医生也是人,一上午看了几十位患者,难免会有倦容呈现。如果医生在回答我的问题时流露出不耐烦的情绪,我肯定会立刻感受到。但我不会发火,而是闭上想询问的嘴巴,尽快结束谈话。我不会要求医生在一上午滴水未进情况下还对我百问不烦。实际上,当看到医生的倦容时,我更多的是感到心疼,我知道他太累了!不耐烦是身体对疲倦的本能反应,而这时,作为一名患者,如果继续用无关紧要的问题贪婪地占有医生的时间,是不是也有些冷酷呢?我们患者也要有一种人文精神。”
“另外,我也尽量要求自己看病时不去托人,不走后门。因为这对别人很不公平。”梁晓声说。2016年前后,梁晓声的胃出了“问题”,于是他平生第一次前往肿瘤医院就诊。医院很大,患者很多,梁晓声有些不知所措,于是,他请肿瘤医院一位相识的领导带他去做检查。虽然那位领导提前和医生打了招呼,但在“插队”时,梁晓声还是明显地感到了医生和患者眼中流露出的反感。他说:“从此之后,我就要求自己,既然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现状,那么,我的一切都应和普通人一样。我在书里写满道理,却要在生活中到处求人、走后门吗?”
文学,只是一味“药”
“目前,仅北京的人口就达到了将近3000万,而医院却基本没有增加。因此,当我们谈文学、文化和医学人文的时候,请不要忘记一个事实——我们的患者实在太多啦!”梁晓声表示,文学、文化与医学人文在面对中国特色的医院时,很难真正落地。
他强调医生要有文学思维,希望医生能够关注科学以外的人性,而不是强求医生让每位患者都感到如沐春风。文学可以作为医学的补充,在文学思维的指导下,医生可以更好地认识疾病、帮助患者。但应注意,过度强调文学对医学的作用也是不可取的。
“毕竟,文学只是一味‘药’嘛!”梁晓声说。
发表评论
最新评论

-

new直播预告丨携手2025 NNDU,汇聚前沿智慧,共探慢病代谢健康新未来
4月26日早8:00,敬请关注
2025-04-25 -
11-202024
征文通知 | 第一届天总-比利时国际重症医学大会暨2024国际脓毒症基础与临床研究学术论坛、2024天津市围术期重症学术年会即将召开
-
11-202024
第一届天总-比利时国际重症医学大会暨2024国际脓毒症基础与临床研究学术论坛暨2024天津市围术期重症学术年会Workshop即将开启
本次大会将开设重症血液净化、ECMO评估与管理、超声评估与穿刺治疗、多模态脑功能监测、气道可视化技术、人工智能助力科研等6场Workshop培训班
-

new第90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博览会(CMEF)即将开幕丨万亿产业新风口,数万新品开启医疗健康新时代
2024-10-09
-

直播预告丨携手2025 NNDU,汇聚前沿智慧,共探慢病代谢健康新未来
2025-04-25 -

直播预告丨2023“一呼一吸 中青年菁英论坛”系列直播(第五十六场)重磅来袭
2023-12-28 -

直播预告丨2023“一呼一吸 中青年菁英论坛”系列直播(第五十三场)来了
2023-12-25 -

直播预告丨2023“一呼一吸 中青年菁英论坛”系列直播(第五十一场)来了
2023-12-18 -

直播预告丨2023“一呼一吸 中青年菁英论坛”系列直播(第四十九场)来了
2023-12-13
-

直播预告|“心关爱 九州行”2023起航!陆林院士携各领域专家,共筑心身屏障,携手健康未来!
2023-02-16 -

直播预告|回归优质睡眠,畅享阳光生活!陆林院士携睡眠健康领域众专家,助力健康睡眠
2023-03-13 -

直播预告|“守护新肾力 全民肾健康”2023世界肾脏病日聚焦“狼疮肾”
2023-03-06 -

门诊药房剥离医院可行吗?
2017-08-06 -

注册通知 | 2023年6月8-11日,上海,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临床肾脏病学专委会第二届年会
2023-05-22 -

会议预告|第九届珠江肝胆专科医疗联盟高峰论坛即将召开
2022-09-2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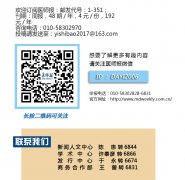
早产儿急性呼吸系统疾病诊治新进展教育项目在全国开展
2017-0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