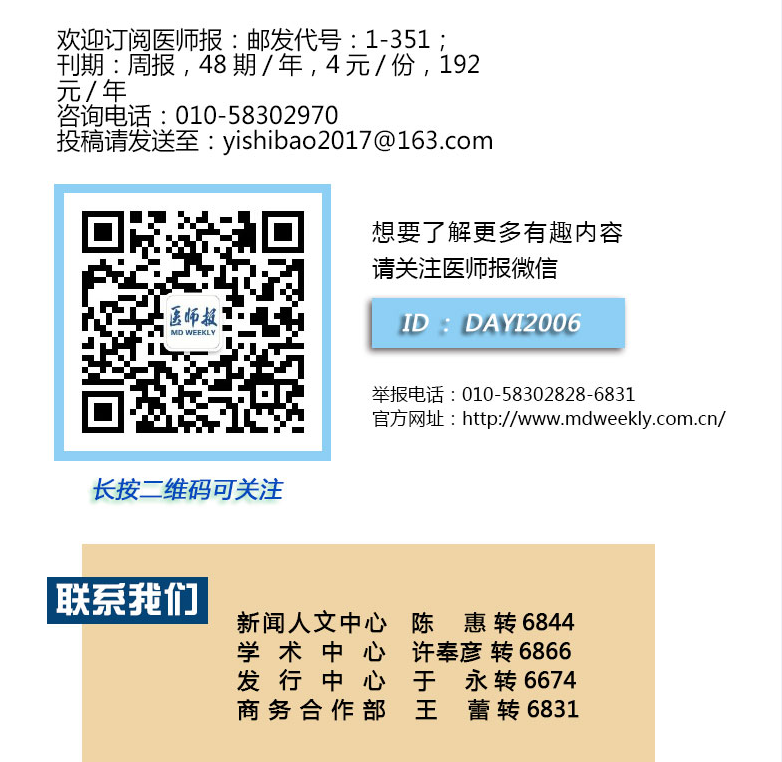关键词 患者教育
提高公众对于癌痛治疗的认识
王杰军:我国晚期肿瘤患者到医院的目标和预期很难实现。欧美国家调查,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到医院后,只有60%希望把病治好,而绝大部分中国晚期癌症患者是希望治愈。如何通过告知,降低患者期望值,告诉他们到医院来不是治愈的,而是改善症状为主,进而改善生活质量,非常重要。
褚倩:前不久,我们抢救一名重病患者,这已经是第五次了,感到回天乏术。患者家属却对我们说:“前四次你们都救活了,这次你们也必须救活。要是救不活,有你们好看。”在很多患者心里,医生就是应该能救活所有患者。
患者和家属过高的治疗期望值需要引导。如果整个社会对于医生、医院抱有过高的期望,那么无论对于医生还是医院甚至整个医疗环境,都不是好事。患者就医的观念需要政府和社会媒体的正确引导。
刘勇:宣教可以从根本上既保护患者又保护医生,让公众及全社会对于医疗行为、医疗常识拥有最基本和正确的认识。
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的Brella教授做了一项调查,他将姑息治疗(palliative care)这个“容易让人产生歧义”的名词改成支持治疗(supportive care)后,转到支持治疗系统中的患者比例上升了41%。在美国,人们提到姑息治疗,也会将其与临终关怀(hospice care)联系在一起。
法律有滞后性,呼吁从个人、医院、协会到国家的层面上宣传教育,使大众认识到吗啡的使用是癌痛治疗的一部分,癌痛治疗仅仅是姑息治疗的一部分,我们需要提高公众的认识,提高患者的认识。当大家对于诸如吗啡一类的药物,有了正确的认识后,就会从根源上杜绝很多纠纷的发生。
其实说到底,问题的根源都在于教育。
刘波:患者教育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我们的南丁格尔志愿团队中,几乎每天下午每个科室都会有不同形式的宣教活动,甚至会把癌痛拍成情景剧,向患者介绍我们是如何去做的,不用担心吗啡成瘾、副作用等问题。总之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患者更加了解疾病、更加了解医生做了什么。
改变社会旧有的错误观念
陈钒:本例诉讼的发生其实与社会观念直接相关,因为大众的普遍认知中,吗啡并不是一个好东西,而是毒品,能上瘾,甚至有人会认为是毒药。很多错误观念的出现,并没有得到及时矫正。
故此,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致使很多与医疗相关内容的不完善。这就需要我们去改变旧有的错误观念。关键是怎么改。
错误的观念是精神层面的问题。我们需要通过一种方法去告诉患者某一种药物是安全的。首先就需要在我们自己的领域内形成专家共识,并建立起这样一种共识的宣传机制。之后再从领域内向全社会传播,告诉大家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社会观念要想改变绝非易事,是一个系统工程。专业人士要形成行业内的共识,政府层面搭建好平台,更重要的是如何将这种想法渗透给老百姓。此时媒体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有些影片中,可以看到因患癌惧怕疼痛而跳海的画面。这种观念其实完全是错误的,对于老百姓的影响更是根深蒂固。因此,媒体通过宣传改善大家的观念,任重道远。
刘端祺:我国是唯一因为鸦片在本土打过两次战争的国家,对吗啡的恐惧心理深深根植于我们的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以刮骨疗毒为代表的忍痛文化一直被我们歌颂,而我们常常忽略了这种歌颂有时是片面的、有害的。
所以,对吗啡的正确使用首先是一种观念的变革,一种民族文化的充实和再认识。我认为,这是我们在这里讨论这个案例的文化价值所在。今后的某个时候,在我国的某个地方,难免会出现一个或几个滥用阿片类药物的刑事案件,如果我们有了这种文化层面带有移风易俗意义的认知,就不会让几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我们的肿瘤治疗队伍、止痛队伍就不会乱了阵脚,一定会淡定处置,继续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关键词 双重效应
宁晓红:吗啡在临床应用前的沟通十分重要,非缓和医学相关科室的医生或者患者,容易在吗啡的用量和使用方法上产生异议。因此医生在与家属沟通时应该明确告知吗啡的“双重效应”,即使用吗啡的目的是为了缓解症状,同时告知不良后果。这种后果是预知的,但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一旦在治疗过程中出现,不能算是医生的过错。
沟通是保护医生最好的手段。只要与患者沟通到位,患者和家属接受吗啡药物的治疗,就不存在任何禁忌。医生应该学会沟通,学会运用伦理学将道理说通。
其次,病程记录应该成为保护自己的武器,将与家属沟通的具体内容记录下来,包括用药目的,如何与家属沟通以及家属如何回应等具体内容,体现出“人情味儿。”
关键词 医疗鉴定
“医疗鉴定不规范不专业”
最终受伤害的是患者
王杰军:鉴定、法院判决,如何能做到更加合理,更加规范?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去探讨。
樊碧发:我国现在没有太多有关阿片类药物使用类似案例的判决,这让我想起了在法学界有种说法,叫“有律按律,无律按例”,即一类问题的第一个判决将对今后影响深远。
所有的司法都来源于实践,我们正是在为良好的立法提供良好的素材。慢性疼痛的对策是困扰全球的问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立法,慢性疼痛是人权,不能只喊口号,要落实到行动上。
宁晓红:在法律判决过程中,要有专业人士参与,例如这个案例至少要有疼痛科使用吗啡的专家,如果都不懂吗啡,如何能够做出正确的判决。
方红:类似于这样专业领域内专家讨论都存在异议的情况,希望在鉴定过程中除了鉴定专家以外,是否能有其他途径,例如成立相关医疗顾问委员会,或邀请相关领域内专家进行讨论。
一个关于吗啡应用的判例的产生,会对今后的医疗行为产生很大影响。如果判断错误,大部分医生可能就不再给患者使用吗啡,就会少了一种缓解患者病痛的途径,最终受害的还是患者。
刘端祺:我留意了一下最近全国范围内的不少医疗鉴定结论,绝大多数断定医方“轻微过错”或“轻微责任”,有的确实医方有“轻微”问题,也有不少明显是“鸡蛋里面挑骨头”。
要命的是,一旦鉴定确立,就非常权威,虽有申诉机会,有时理由也很充分,但那个结论的权威性往往不可撼动,难以改变,成为法官判决的依据。如果这种“‘轻微’模式”成为医疗鉴定的常态,无疑将是我国医院的灾难。
按现行法律,这个“轻微”很“值钱”,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甚至更多。有的医院和医生之所以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也是因为没地方说理,只好赔钱了事。这就使一些医闹或怀有一些不良企图的人,把告医院当成非常随便而且比较容易来钱的行为。
需知,绝对正确的治疗和绝对完美的病历是不存在的,要想找出点“轻微问题”并不难。事实上,在北京已经有睾丸癌治愈十几年后状告医院诊断错误(理由是癌症为什么活这么长),尽管证明诊断不错,仍因“告知不充分”获赔数十万元的例子。此风万不可长,否则,社会上将很快有人发现这个“秘密”,医院将成为风声鹤唳之地。
所谓的“第三方医疗鉴定”据说只有中国才有。我们有时应该反思这种鉴定的存在是否合理,它到底应该如何存在。这是此案之外的题外话,当然,其实也不是题外话。参加这种鉴定的医生需要掌握多少专科知识、紧跟多少医疗前沿进展?但是,目前在中国、在世界,有这样的万能医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