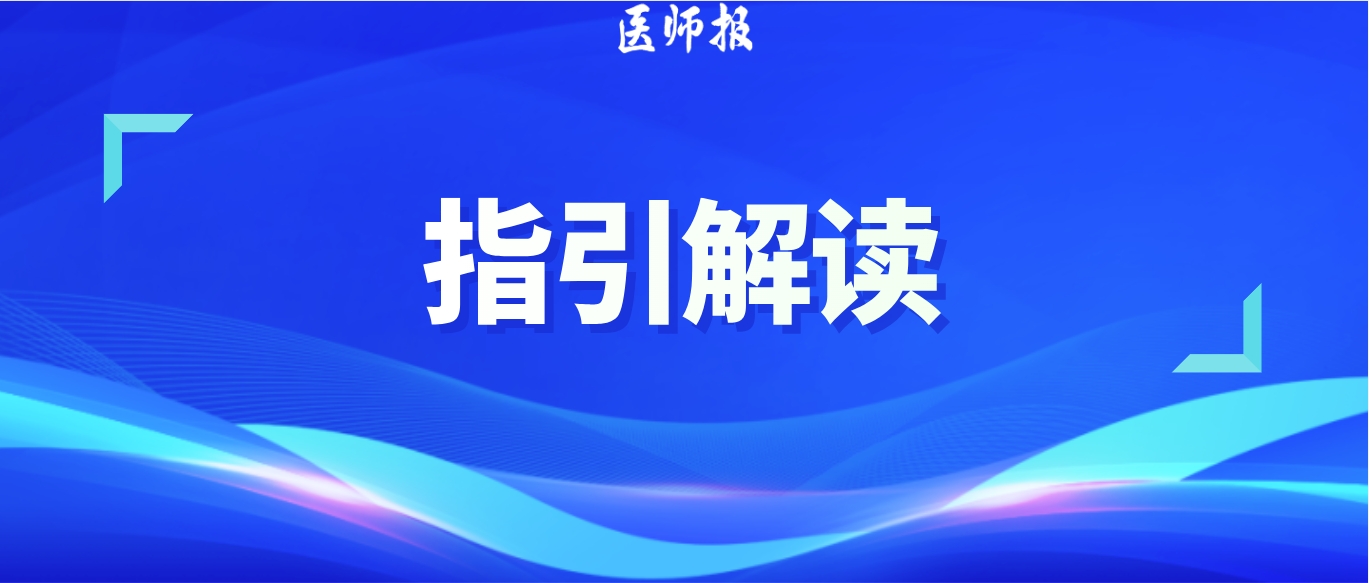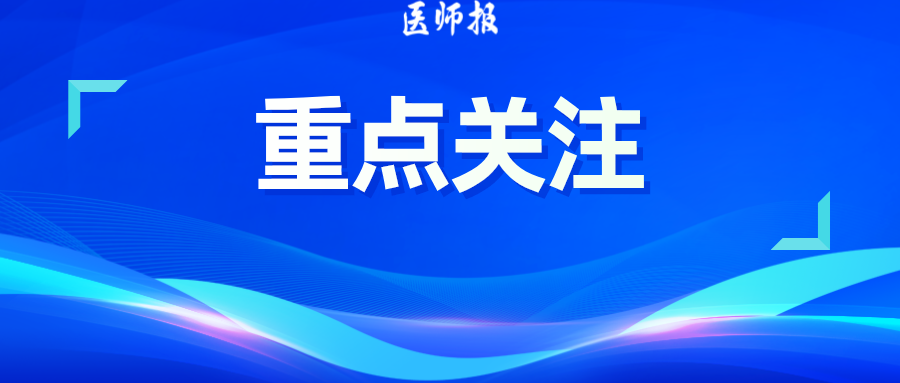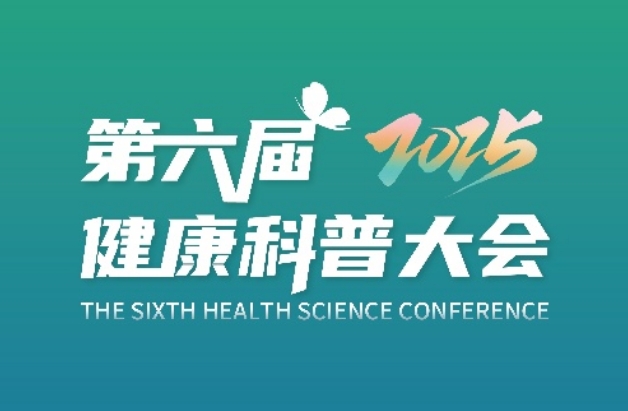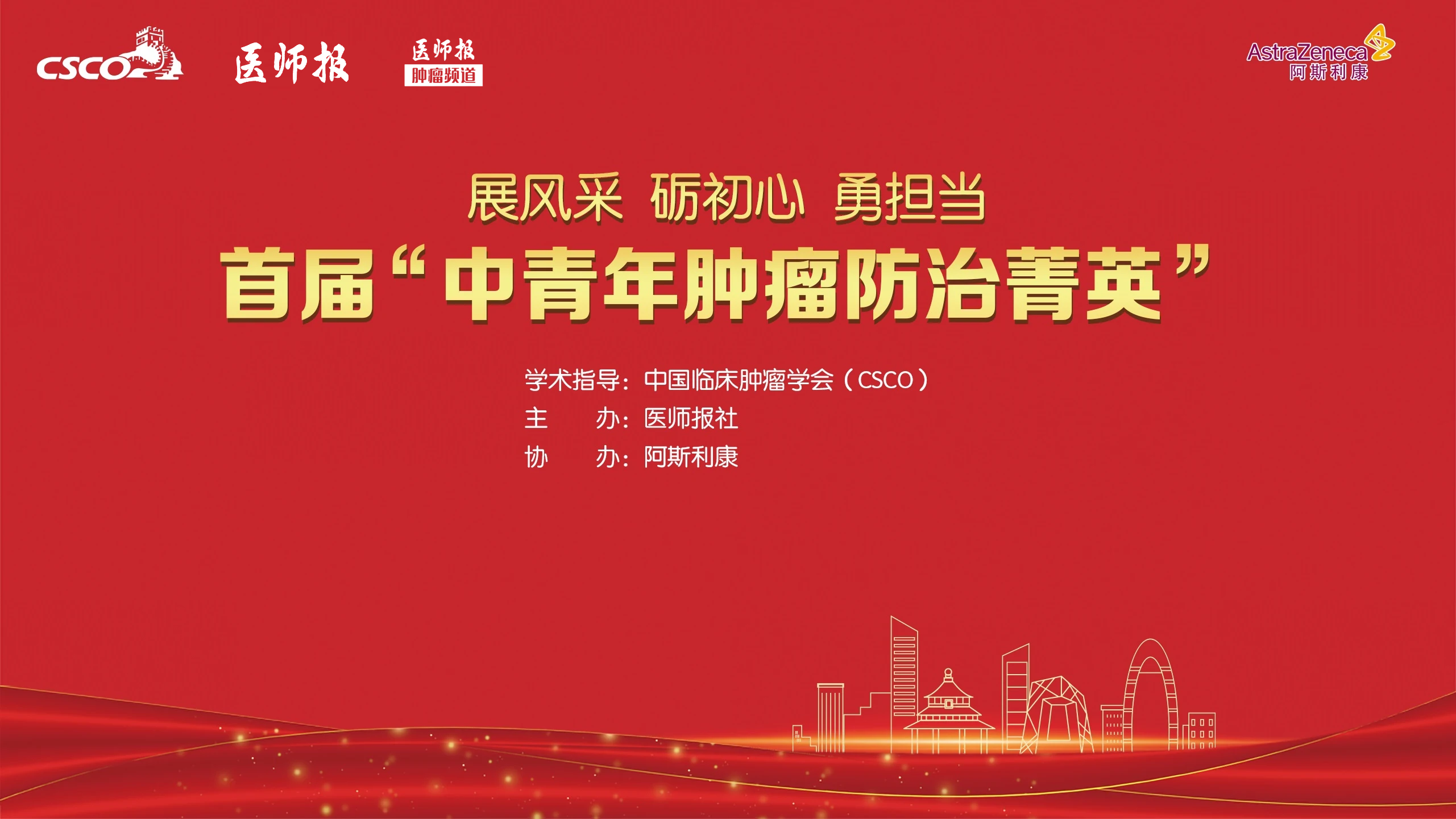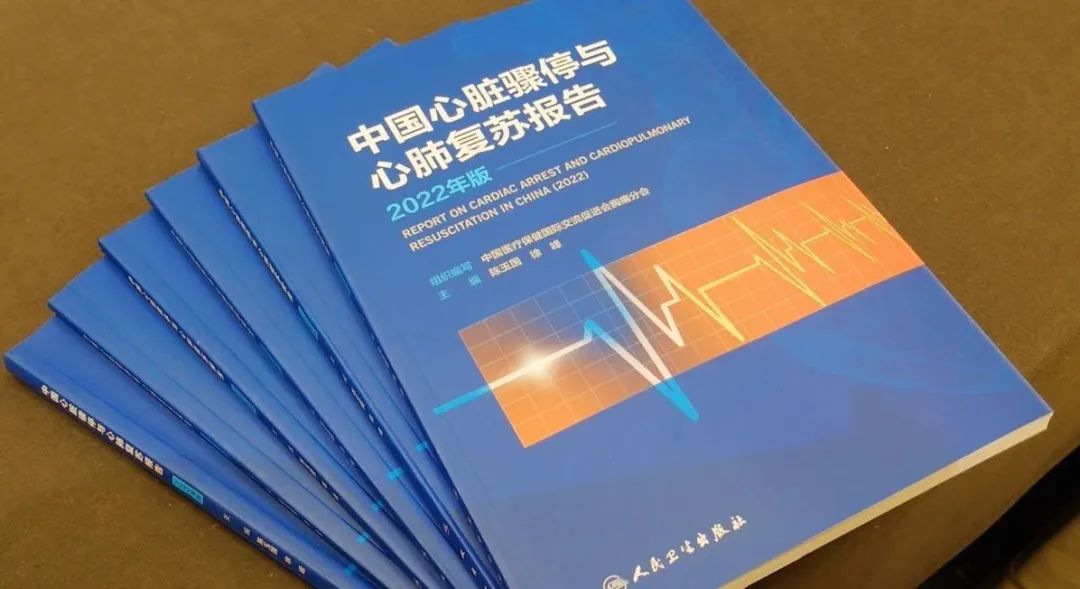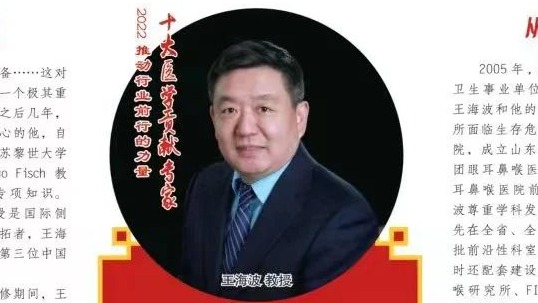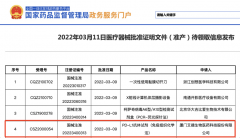本文作者: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山缨 李勇
2017年美国心脏协会(AHA)和美国心脏病学会(ACC)联合发布的高血压管理指南,将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下移至收缩压(SBP)≥130 mmHg和/或舒张压(DBP)≥80 mmHg,且降压目标也下移至<130/80 mmHg,激起了全球高血压领域的热切关注和讨论。
之后的近10年,多项关于强化降压目标的重磅RCT研究及系统性评价研究结果的问世。日前,AHA/ACC更新了成人高血压预防、评估和处理指南(简称“2025年美国新指南”),本文对指南更新要点及对我国高血压防控工作的借鉴意义进行解读。

李勇 教授

山缨 教授
2025年美国高血压指南推荐重点
2025美国新指南不仅沿用了2017年版指南的诊断和治疗基本原则,且部分推荐建议更积极,在生活方式干预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及早降压药物干预。
1、 高血压诊断标准
成人高血压诊断标准为诊室血压SBP≥130 mmHg和/或DBP≥80 mmHg。
SBP 130~139 mmHg和/或DBP 80~89 mmHg者为高血压1级。
SBP≥140 mmHg和/或DBP≥90 mmHg者为高血压2级。
家庭自测血压和动态血压监测作为诊断高血压的金标准。
2、 生活方式干预
减重、DASH饮食模式、钠元素<2300 mg/天、增加钾摄入、限酒、每周≥150分钟有氧运动和阻力训练等。
3、 不同危险分层患者的药物干预时机
对个体高血压患者的药物诊疗,不仅根据血压水平,还需结合其心血管病危险分层。
血压≥140/90 mmHg的所有成人患者,立即启动降压药物治疗(ⅠA)。
SBP 130~139 mmHg(ⅠA)或DBP 80~89 mmHg(ⅠC)者,若已存在临床心血管病,应立即启动药物降压治疗。
SBP 130~139 mmHg(ⅠA)或DBP 80~89 mmHg(ⅠC)者,若无临床心血管病,但存在糖尿病或慢性肾病或心血管风险增高者(PREVENT评分10年心血管病估测风险<7.5%),立即启动药物降压治疗。
SBP 130~139mmHg(ⅠBR)或DBP 80~89mmHg(ⅠBR)者,若无临床心血管病,且PREVENT评分10年心血管病估测风险<7.5%者,3~6个月生活方式干预后,SBP仍≥130mmHg者,可考虑给予药物降压治疗。
4、降压药物的选择
一线降压药物包括利尿剂(氯噻酮、吲达帕胺)、钙拮抗剂、ACEI和ARB。
对于高血压2级患者,为提高降压达标率和依从性,推荐采用由2种一线降压药物组成的单片复方制剂作为起始降压治疗药物(ⅠBR)。
5、 降压目标
大多数高血压患者,推荐SBP至少<130 mmHg,鼓励进一步控制SBP<120 mmHg(ⅠA)。
大多数高血压患者,推荐DBP<80 mmHg(ⅠBR)。
2025美国新指南对我国高血压防控的借鉴意义
1、 引用5项国人研究强化降压证据坚实
2025美国新指南最大的特点是降压目标更积极,不仅推荐大部分高血压患者降压目标SBP<130 mmHg,更鼓励进一步SBP<120/80 mmHg。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研究证据的逐步积累,降压目标不断下移。90年代起,临床实践都遵循降压目标<140/90 mmHg。
2025美国新指南中,降压目标推荐的支撑证据有5项重量级降压目标RCT研究(SPRINT研究、STEP研究、ESPRIT研究、BPROAD研究以及CRHCP研究),后4项都为来自中国人群的研究结果。
01 SPRINT研究
纳入50岁以上SBP>130 mmHg的不伴糖尿病和卒中的高心血管风险患者,经过3.26年随访,强化降压组(降压目标SBP<120 mmHg,研究结束时平均血压121.4 mmHg)较传统降压组(降压目标SBP<140 mmHg,研究结束时平均血压136.2 mmHg)主要心血管事件发生率下降25%,且年龄>75岁的高龄老人,亦从强化降压中显著获益。不过,该研究亚洲人群比例极低(<2%)。
02 STEP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蔡军教授领衔的STEP研究结果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研究纳入了来自中国42个研究中心的8511例老年高血压患者(60~80岁),按1∶1随机分入强化降压组(目标SBP为110~130 mmHg)和标准降压组(目标SBP为130~150 mmHg)。研究基线时血压142.0/82.5 mmHg,年龄≥75岁占比28%,糖尿病史者29%,既往心血管病史者6.3%,eGFR<60 ml/min/1.73 m2者2.4%,未纳入卒中患者。因此,该受试者群体中以一级预防高血压患者居多。研究中位随访时间3.4年,因两组间主要心血管不良终点事件发生率差异显著而提前终止。
受试患者在随机分组1年后,强化降压组和标准降压组平均SBP分别降至127.5 mmHg和135.3 mmHg。强化降压组主要终点事件较标准降压组显著下降26%(HR 0.74;95%CI 0.60-0.92;P=0.007)。STEP研究是我国老年高血压患者强化降压至SBP<130 mmHg的坚实支持证据。
03 ESPRIT研究
ESPRIT研究以我国50岁以上心血管病二级预防人群为主体受试者,研究结果发表于Lancet杂志。
研究入选已有心血管病史或高危心血管风险的SBP 130~180 mmHg的高血压患者11 255例(糖尿病史者38.7%,卒中史者19.2%,既往心血管病者29%),按1∶1随机分入降压目标SBP<120 mmHg和SBP<140 mmHg组,中位随访3.4年。受试者平均年龄为64.6岁、基线SBP147 mmHg。
研究结果显示,强化降压组的SBP为119.1 mmHg,标准降压组的SBP为134.8 mmHg。研究结果提示,降压目标SBP<120 mmHg组较SBP<140 mmHg组进一步降低主要心血管事件发生率12%(HR 0.88;95%CI 0.78-0.99;P=0.028)。强化降压组的心血管事件获益一致性体现在有或无糖尿病史者、以及有或无卒中史者中。ESPRIT研究为高血压患者降压目标进一步降低至<120 mmHg 提供新的循证证据。
04 BPROAD研究
糖尿病人群降压目标一直是高血压领域研究的热点,ACCORD-BPLT研究结果表明,与标准降压治疗组(目标SBP<140 mmHg)相比,强化降压治疗组(目标SBP<120 mmHg)并未显著降低主要复合心血管事件(心梗、卒中和心血管死亡)的风险,但卒中发生风险显著降低达41%。随后多项Meta分析提示,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更积极的降压治疗策略能带来更显著的临床获益。
2024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宁光教授公布了糖尿病人群降压目标研究(BPROAD)研究结果,同时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在线发表。
研究入选50岁以上2型糖尿病、SBP在130~180 mmHg(已用降压药物者)或SBP≥140mmHg(未用降压药物)、且伴心血管风险因素的患者12 821例,按1∶1比例随机分入SBP<120 mmHg组或SBP<140 mmHg组治疗5年。患者平均年龄63.8±7.5岁,随访1年时,强化降压组和标准降压组血压分别达到121.6 mmHg和133.2 mmHg。
结果显示,强化降压(SBP<120 mmHg)组较标准降压(SBP<140 mmHg)组主要心血管终点事件发生率显著下降21%(HR 0.79;95%CI 0.69-0.90)。研究不仅为糖尿病人群强化降压提供获益证据,更为广泛高血压患者进一步强化降压目标至SBP<120 mmHg提供临床证据。
05 CRHCP研究
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孙英贤教授领衔的CRHCP研究聚焦农村地区基层医疗的高血压管理,发表于Lancet杂志。
CRHCP研究是一项前瞻性开放标签、終点事件盲法评估、集群随机对照试验,在中国326个村庄进行,并追踪3年。
受试者年龄≥40岁,未治疗的SBP≥140 mmHg或DBP≥90 mmHg;若有高心血管风险或已有治疗史,SBP≥130 mmHg或DBP≥80 mmHg。以村庄依照省、市、镇层级随机分配至干预组或对照组,两组各163 个村庄,共33 995名参与者。
以乡村卫生工作者主导执行多面向干预,包括按照简化「阶梯式医疗」方案启动及调整降压药,目标SBP<130 mmHg和DBP<80 mmHg;提供优惠或免费降压药物;健康教育、生活方式指导(如家庭血压监测、用药依从性);基层医师定期监督指导。主要复合终点为心梗、卒中、因心衰住院、或心血管死亡。
CRHCP研究结果显示:干预组与对照组血压分别降至126.1/73.1 mmHg和147.6/82.3 mmhg。与对照组相比,干预组主要复合終点发生风险显著降低33%(HR 0.67,95%CI 0.61–0.73,P<0.0001)。此外,心梗风险降低23%(HR 0.77,95%CI 0.60–0.98,P=0.037);卒中风险降低34%(HR 0.66;95%CI 0.60–0.73,P<0.0001);心衰风险降低42%(HR 0.58;95%CI 0.42–0.81,P=0.0016);心血管死亡风险降低30%(HR 0.70;95%CI 0.58–0.83,P<0.0001);全因死亡风险降低15%(HR 0.85;95%CI 0.76–0.95,P=0.0037)。充分证实了在农村基层医疗实践中强化血压管理的有效性、可及性和重要性。
从SPRINT研究到STEP、ESPRIT和BPROAD研究以及CRHCP研究,均一致显示对高危心血管风险的高血压患者,采取更加积极的降压治疗策略,更严格的血压管理,能够为高血压患者带来更大的心血管临床获益。
上述5项研究中的STEP、ESPRIT、BPROAD和CRHCP等4项临床研究均以我国高血压人群为研究对象,涵盖了老年及高龄人群、心血管一级预防人群以及糖尿病人群和卒中等二级预防人群,为解决高血压降压目标值这一重大科学问题提供了依据,充分证实以<130/80 mmHg为目标(合并心血管病或糖尿病者SBP<120 mmHg)的强化降压方案可以在全人群中显著降低心血管事件和全因死亡率,并进一步揭示了以村医为主导的多层面干预措施是高血压患者管理的有效模式。
从安全性角度来看,与SPRINT研究相似,来自中国的4项研究中,强化降压组的低血压发生率均显著高于标准降压组,但从绝对数值来看绝大多数患者都能耐受强化降压,受试者失访率都较低,跌倒骨折及严重肾脏损伤均无差别。因此,权衡利弊,强化降压治疗从整体上来看还是能带来更多的心血管绝对获益。
这次2025美国高血压新版指南以我国的多项临床试验结果为依据,再次说明我国高水平临床试验已成为我国乃至世界高血压防治和管理的重要来源。因此SBP<130 mmHg,并进一步鼓励SBP<120 mmHg,理应成为适合中国大部分高血压人群的降压目标。
2、 启动降压药物治疗时机显著前移
我国2024版高血压指南也提出启动降压药物治疗的时机不仅单纯依据血压水平,还需取决于个体心血管风险,不过我国指南推荐的降压药物启动时机相对比较保守,如血压≥160/100 mmHg的高血压患者,才立即启动降压药物治疗(ⅠA)。SBP 140~159 mmHg(ⅠA)或DBP 90~99 mmHg(ⅠC)者,心血管风险为中危以上者才立即启动药物降压治疗,而对单纯血压≥140/90 mmHg者,仍建议先行生活方式干预4~12周,若血压仍不达标,才考虑启动降压药物治疗(ⅠC)。
2025年美国新指南推荐所有≥140/90 mmHg的患者,均应立即启动降压药物治疗。前移的启动降压药物时机是否适合我国人群?
2008年发表的我国40岁以上17万人群观察型研究结果提示,我国人群血压水平和心血管病的显著线性相关关系从SBP>110 mmHg就已开始,收缩压≥140 mmHg和/或舒张压≥90 mmHg者,其10年心血管风险已达15%,即意味着40岁以上血压>140/90 mmHg的患者已经属于心血管风险高危。此外,我国门诊高血压患者中,80%~90%都伴有1种以上心血管危险因素。因此,血压高于140/90 mmHg的成年患者,大部分心血管风险都在中高危以上,尽早启动降压药物治疗,能尽早心血管获益。
中美高血压指南对SBP 130~139 mmHg、心血管风险为高危和很高危者,立即启动降压药物治疗这项推荐是一致的(ⅠB),但SBP 130~139 mmHg心血管风险低危和中危患者,中国2024年指南推荐持续进行生活方式干预。而2025美国新指南推荐,3~6月的生活方式干预后,仍SBP>130 mmHg者,应启动降压药物治疗,以减缓患者的靶器官损伤。
当前,针对SBP 130~139 mmHg伴心血管风险低、中危人群中,药物降压是否能带来远期心血管事件获益的研究很少,因此,国内外指南对这类患者的一致推荐是生活方式干预,但临床实践和临床研究都发现,单纯生活方式干预很难长期维持血压在理想水平。
2016年,一项巴西人群进行的高血压前期患者预防高血压的随机双盲对照研究(PREVER-Prevention)发表,血压120~139/80~89 mmHg者进行3个月生活方式干预后,随机分入利尿剂组或安慰剂组,18个月后,利尿剂组高血压发生率较安慰剂组下降44%(11.7%和19.5%,HR 0.56,95%CI 0.38-0.82),利尿剂组左室肥厚程度逆转显著优于安慰剂组。
因此,美国新版高血压指南前移启动降压药物治疗时机的策略,是为了尽早预防血压对靶器官的损害。当然,我国人口基数庞大,而成人高血压患者(>140/90 mmHg)的患病率高达27%,因此,对SBP 130~139 mmHg、心血管病低、中危人群也纳入降压药物治疗人群,也要从药物经济学、药物可及性、以及人群接受度等实际状况考量。
但是CRHCP研究以及来自北京安贞医院赵冬教授团队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目前指南里推荐的一线/首选降压药物均已进入医保和国家集中采购目录,国家集采后的降压药物价格极为低廉,药物经济学上已经具有极大的价值。目前,我国所有一线降压药物均已进入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中心的处方范围,可及性可以完全覆盖。因此,强化血压管理,所有确诊的高血压患者(中国指南血压≥140/90 mmHg)均立即启动降压药物治疗,是完全可行的。
鉴于目前我国心脑血管病的发病率和致死率仍呈上升的势头,及早启动降压药物治疗,并且将血压控制到至少<130/80 mmHg,SBP最好<120 mmHg至关重要,且刻不容缓。
3、推荐起始单片复方制剂降压治疗
多种机制的降压药物联合应用能显著提高患者达标率、降低单一药物剂量增加而产生的不良反应。既往国内外高血压指南大多推荐血压>160/100 mmHg患者,起始就可两种以上降压药物联用,必要时可选择单片复方制剂(SPC)。但在降压目标进一步下移到<130/80 mmHg,并鼓励血压 <120/80 mmHg时代,SBP≥140mmHg和/或DBP≥90mmHg患者基本都需要2种以上降压药物才能血压达标,如强化降压RCT研究(SPRINT研究和STEP研究),受试者都同时联合使用至少2种以上的降压药,才能控制SBP<130 mmHg。
2025美国新指南对SBP≥140mmHg和/或DBP≥90mmHg患者直接推荐SPC作为起始治疗,且列为Ⅰ类证据推荐,现今是国内外高血压指南中的首次。
SPC服药便利,医疗支出较低,与两药自由联合的降压策略相比,SPC能更有效地提高患者用药依从性、改善血压控制水平,降低心血管事件发生。如北加州Kaiser医疗系统在2001年SPC使用率不足1%,2009年提高到27%,血压达标率也从43.5%上升至80.4%。美国另一真实世界研究发现,与单药治疗后加用第二种药物治疗相比,起始SPC者急性心梗、卒中、因心衰住院治疗和死亡复合风险显著下降34%,这与患者用药依从性及血压达标直接相关。
现行的中国高血压指南中推荐的降压目标为<140/90 mmHg,若患者能够耐受,可降低到<130/80 mmHg。因此,为了促使我国高血压患者尽早血压达标,提升长期用药的依从性,改善心血管病预后,起始SPC治疗也适用于我国患者。
4、推荐PREVENT方程评估心血管风险
2025美国指南推荐PREVENT方程估测10年心血管风险。PREVENT模型是根据吸烟、SBP、总胆固醇水平、已采用降压药物、已采用他汀、糖尿病、eGFR水平这7个变量计算个体心血管风险。PREVENT评分<5% 为10年心血管低危,5%~7.5%为10年心血管低中危, 7.5%~10%为10年心血管中高危,>10%为10年心血管高危。
美国心血管风险预测模型,有80年代的Framinghan risk model,2013年的Pooled Cohort Equation(PCEs)以及2024年初启用的PREVENT Equation,通过前瞻性预测能力比较,PREVENT Equation 预测心血管风险准确率显著优于PCEs。
PREVENT Equation是收集1992-2017年美国25个数据库328万人群数据,平均随访4.8年,将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ASCVD)死亡、因心衰住院或死亡作为终点事件,做出10年-、20年-、30年-的心血管风险估测模型。
PREVENT Equation优于既往PCEs Equation模型的原因是:(1)被研究者为现今医疗水平下的人群;(2)未纳入冠脉支架置入等心血管事件,因为不同医疗机构PCI等指证不同,它更多以心血管死亡相关的硬终点为研究目标;(3)将心衰住院或死亡也列为研究终点。随着医疗进步,人口老龄化,心衰已成为影响人群生活质量和生存预期的另一疾病负担;(4)纳入eGFR信息;(5)舍弃了人种变量,更加简单化。PREVENT Equation研发中,已纳入各种族裔,白种人78%,黑人10%,亚裔2.6%。从这些特点来看,未来PREVENT Equation将成为美国临床心血管风险评估的主要工具。
近10多年来,我国学者也研发了来自中国人群的ASCVD风险模型China-PAR,纳入变量包括年龄、治疗或未治疗的收缩压水平、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当前吸烟状况、糖尿病、腰围、南北方区域等,但该模型没有纳入心衰、肾功能等与心血管预后密切相关的信息。因此,美国PREVENT Equation模型能否指导我国人群的心血管风险评估,尚需在我国人群中进行前瞻性验证。同时,研发源于我国人群数据的心血管风险预估新模型也是当前的迫切需求。
高血压是心脑血管病致残和致死的首要危险因素。我国人群以SBP>140/90 mmHg为标准标准的高血压患病率已接近27%,随着循证证据的日益丰富,无论是对一级预防的人群,还是对已有心血管病或高危风险的人群,血压目标下移至130 mmHg以下,都已得到充分论证。
更重要的是,支持2025年美国高血压指南的血压强化管理目标的临床证据主要就是来自我国临床试验的结果。因此,我们应该树立自信,根据国人研究证据,大力倡导及早降压药物治疗和强化血压管理,这对我国高血压人群,包括SBP 130~139 mmHg的正常高值人群,及全社会的心血管健康水平提升,都具有极其重大且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