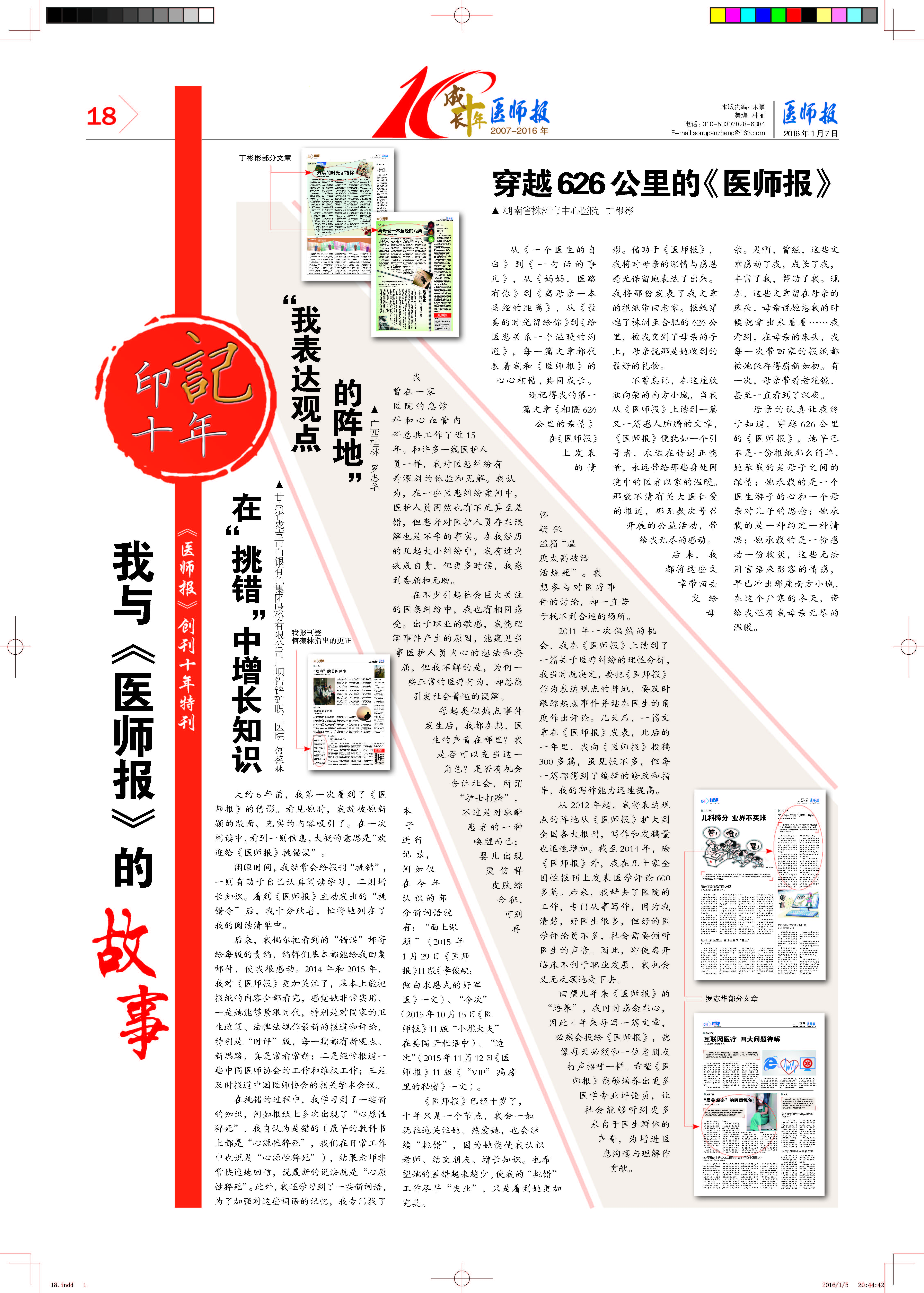我曾在一家医院的急诊科和心血管内科总共工作了近15年。和许多一线医护人员一样,我对医患纠纷有着深刻的体验和见解。我认为,在一些医患纠纷案例中,医护人员固然也有不足甚至差错,但患者对医护人员存在误解也是不争的事实。在我经历的几起大小纠纷中,我有过内疚或自责,但更多时候,我感到委屈和无助。
在不少引起社会巨大关注的医患纠纷中,我也有相同感受。出于职业的敏感,我能理解事件产生的原因,能窥见当事医护人员内心的想法和委屈,但我不解的是,为何一些正常的医疗行为,却总能引发社会普遍的误解。
每起类似热点事件发生后,我都在想,医生的声音在哪里?我是否可以充当这一角色?是否有机会告诉社会,所谓“护士打脸”,不过是对麻醉患者的一种唤醒而已;婴儿出现烫伤样皮肤综合征,可别再怀疑保温箱“温度太高被活活烧死”。我想参与对医疗事件的讨论,却一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场所。
2011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医师报》上读到了一篇关于医疗纠纷的理性分析,我当时就决定,要把《医师报》作为表达观点的阵地,要及时跟踪热点事件并站在医生的角度作出评论。几天后,一篇文章在《医师报》发表,此后的一年里,我向《医师报》投稿300 多篇,虽见报不多,但每一篇都得到了编辑的修改和指导,我的写作能力迅速提高。
从2012 年起,我将表达观点的阵地从《医师报》扩大到全国各大报刊,写作和发稿量也迅速增加。截至2014 年,除《医师报》外,我在几十家全国性报刊上发表医学评论600多篇。后来,我辞去了医院的工作,专门从事写作,因为我清楚,好医生很多,但好的医学评论员不多,社会需要倾听医生的声音。因此,即使离开临床不利于职业发展,我也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回望几年来《医师报》的“培养”,我时时感念在心,因此4 年来每写一篇文章,必然会投给《医师报》,就像每天必须和一位老朋友打声招呼一样。希望《医师报》能够培养出更多医学专业评论员,让社会能够听到更多来自于医生群体的声音,为增进医患沟通与理解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