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已建立起四大注册登记系统,公开透明的捐献体系、分配体系和监管体系。具备国家准入标准的移植医院有169家。”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表示,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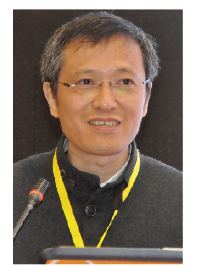
陈静瑜 教授
挑战一:患者观念落后
国外肺移植是改善生活质量的手术,而在国内,却是濒死患者为救命而做出的选择。
据陈静瑜介绍,目前在受者当中做得最多是特发性肺纤维化(IPF)患者,占50%,在国外IPF患者占26%,肺气肿患者占28%。有的IPF患者病情迅速恶化,等不到供肺就去世了。“这是医生最不愿意看到的,”陈静瑜说,因此医生要区分缓慢和快速进展,总结经验,什么样的患者需要保守治疗,让其稳定,什么样的患者要及时评估肺移植。
挑战二:器官有效利用率有待提高
陈静瑜表示,公民逝世后多器官捐献中对于心肺器官的有效利用率仍有待提高。“2016年,共计4080名患者捐献了11296个器官,但肺的利用率只有5%,与国外20%~25%的肺源利用率仍存在很大差距。”他希望ICU医生对脑死亡并有潜在捐献器官意愿的患者,加强脏器保护,最终实现多器官捐献,让生命得以延续。
捐献的器官需要评估,陈静瑜说,在我国所有的患者都是插着管子,在呼吸机支持下进行器官捐献评估,再选择器官。这对于肺评估而言,是不小的挑战。“肺评估难,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肺移植做得少的原因。”
挑战三:就近获取器官就近移植
交通的保障是关键。2016年5月6日器官转运绿色通道文件下发,对中国做器官移植有里程碑的贡献。
“当前我国器官都是远距离转运,原国家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说过,全国有26家肺移植准入医院,我们要增加更多的肺移植准入试点,开放一批愿意做肺移植的医院,让器官捐献获取医院做得比较好的医院来做肺移植。这样肺移植才可以实现在当地获取当地移植。”陈静瑜说。
挑战四:多学科团队配合
只有多器官获取,才使患者的爱心能够拯救更多的患者。而把患者的爱心充分扩大,需要有团队配合。
肺移植患者长期存活主要是靠团队,这个团队需要胸外科医生、呼吸科医生、ICU医生、病理科医生、医技检验医生、康复理疗师,甚至心理医生。
陈静瑜说,外科医生手术完成,接下来要靠ICU、呼吸科医生。他们要防止术后30天之内可能产生的感染和术后早期原发性移植物失功(PGD)导致的死亡。“目前我们已经可以控制PGD,感染成为主要原因。”
此外,要加大对医生的培训,让供体器官得到准确评估、运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