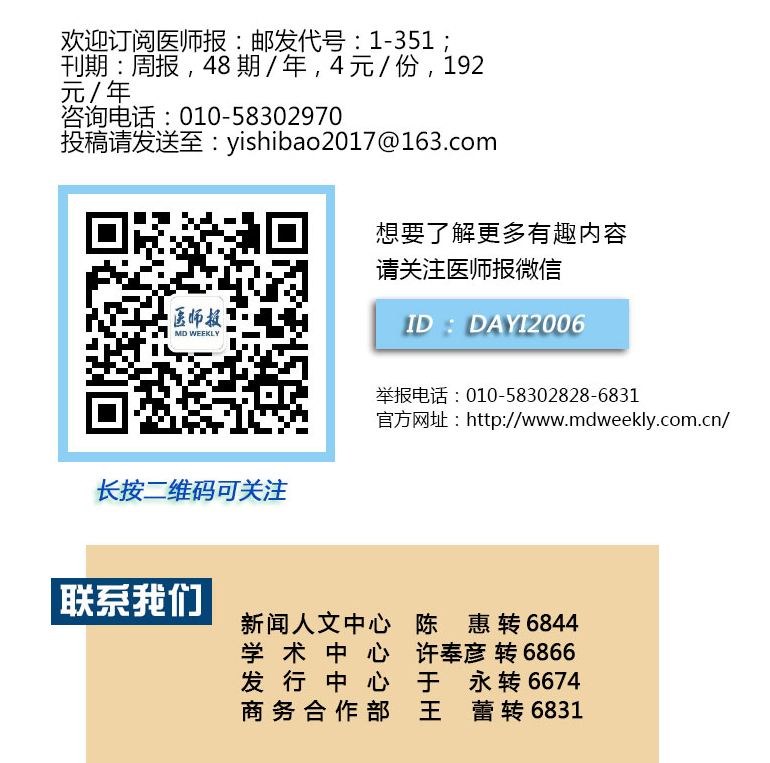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清明已过,但追思犹在。
“死亡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咱们思考得太少了,有时甚至是在刻意回避这个必然的问题。面对着预料之中或者突如其来的死亡,总是那么惊慌失措,不知所以,甚至无知无觉地逝去……”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医患关系协调办公室主任樊荣,回忆起大学时代王岳教授的一堂关于生死的课程,由衷感慨。
樊荣说,死亡是我们每个人的最终归处,我们应认真思考它。未知死,焉知生。

《我本是树》来源于此书
一堂大学课
让我开始思考死亡
2012年,28岁的樊荣正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就读医学硕士。正是那一年的一堂大学课,让他开始设身处地去尝试触摸和体会“死亡”——这个总是那么容易被自己和身边人忽视的必然问题。
“那是一堂讨论安乐死及舒缓医疗相关问题的课程,王岳教授主讲的《临床医事法》。”樊荣用平缓亲和的声音向我们回忆讲述,把我们带进了当年的大学课堂之中,“课后,王教授向大家提出了问题。”
王教授问,“谁能告诉我,自己死亡大概是什么时候”,下面没人说话。
王教授又问,“谁能告诉我,自己的死亡大概会是在哪个十岁的阶段,六十岁?七十岁?”,下面仍然没人说话。
“所以,我们都说不好。其实,死亡就是随时的、不可预估的、充满偶然性的。我们活着的每一天,都有可能是生命的最后一天……细细一想,其实我们好像都没有认真地想过死亡这个问题,临终前到底希不希望接受有创治疗?愿不愿意做器官捐献?什么事情临死前一定要做?有什么重要的心愿……”
王教授的一系列发问,让樊荣联想到美国的驾照,每份驾照单旁边都会附着捐献卡。诸如遇到意外,你希不希望有创治疗,愿不愿意做器官捐献等问题,樊荣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拨动了关于死亡的思维神经——我们到底是多活了一天,还是向死亡更靠近了一天,临终的有创治疗到底是在挽救病人多活一天,还是在让他多受了一天死亡的折磨。
带着王岳教授布置的课后作业——自己给自己写一份遗嘱,樊荣开始了对于死亡的思考。
4份遗嘱 3次修改
课后一周的一个深夜,樊荣坐在书桌前,第一次为自己拟遗嘱。他郑重写下:“我到终末期失去意识时,不希望进行有创的抢救治疗,顺其自然地死亡就好。我愿意捐献眼角膜。墓葬方式,希望火化之后将骨灰送回故乡的家族墓地之中……请家人不要去追讨朋友××的债务。如果他经济困难,他确实不能还;如果他故意不还,借此认识了一个人也值得。”
2014年,遗嘱中提到的这位借钱的朋友终因四处借债,走上犯罪,东窗事发,当他最终将借款还给樊荣时,樊荣对遗嘱做了第一次修改——删除了朋友债务的有关内容。
2015年,女儿的成长和与日益增的父女之情,令樊荣再次拿出遗嘱,做了第二次修改,他情不自禁地写下:“女儿的人生之路,不要去规定她的发展,快乐就好,她自己想做的事情就让她尽情去做。我希望她拥有一种为而不争的品格,长大成人,做一名知书达理、性格温婉的女性,修己以安人。”
“后来,我又觉得后人想纪念你,其实他怎么都会纪念你,并不用非要弄一块墓碑。我比较喜欢大海,那就海葬吧!”樊荣平静地说,那时,他又把家族合葬的方式变成了海葬。
也许,在樊荣的生命中,一个人死后对于家族的归属,已经变成对这个世界和自我的归属。
直到2016年,一次偶然的机缘,樊荣阅读了余秋雨先生的散文《我本是树》,顿时感悟,可能一棵树的墓葬方式会令他更加欢喜!
“不用在墓园里栽树,在海边栽种一棵树就可以了。希望用榕树,很粗大很宽广,枝繁叶茂,深植于地,相伴于海,契合我内心对‘天下’和‘个体’的一种情怀吧。” 樊荣动情地说,由此,樊荣第三次修改了自己的遗嘱。
我本是树
“遗嘱会让人透视死亡!”樊荣感叹,“写一份遗嘱时,你才发现原来那些放不下的、牵挂的,都是一些外在的东西,都是自己给自己增加的负担,千万别让自己成为欲望的奴隶,那样的活着等于死亡。”
“其实,也只有当你开始思考遗嘱怎么写的时候,你才能真正洞悉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对于我来说,第一就是精神传承,我们的头脑中,生存着无数前辈的意识、理念、文化,其实并没有什么死亡可言,失去的仅是肉体,精神将持续传承。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会传承我的精神。第二是学会放下,放下纷扰的杂念、无用的欲望、无畏的怨念,活得则会更轻松释然。第三是活在当下,当你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只要今天的你比昨天的你有进步,那就是收获。
樊荣顿了顿,低声说道,“我本是树,可能这就是我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