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7-31日, 欧洲心脏病学会(ESC)年会在意大利罗马召开。一开幕,ESC主席Fausto J Pinto的欢迎词引用意大利著名导演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的话,罗马是永恒之城,“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只有对生命的激情。”
在开幕讲演中,Pinto还引用了意大利亚里士多德的名言,说:“幸福是生活的意义和目的,是人类生存的目标和终点。”
但幸福是一个如此虚幻的概念,康德:“幸福是如此不确定的一个概念,以致于尽管每一个人都希望获得幸福,然而他永远都不能够明确地、一贯地说出他真正希望和想要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好在Pinto又引用但丁的话“做事的秘诀是要采取行动”,让幸福的讨论收了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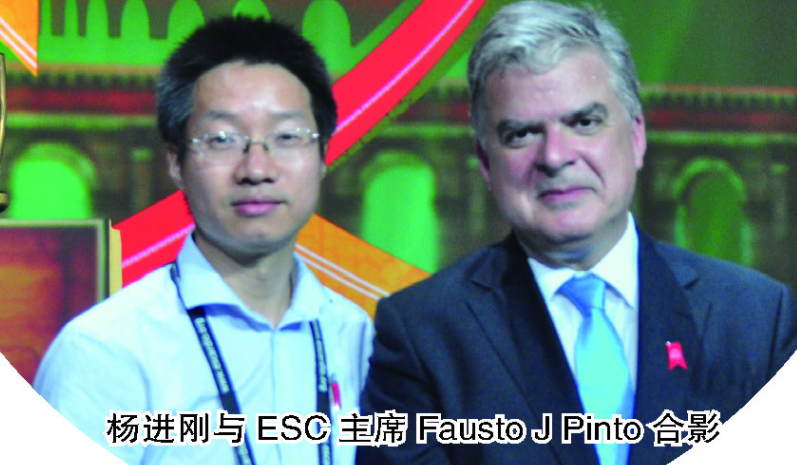
罗马大街小巷遍布累累历史遗迹,超越了时间长河。但罗马更让人惊奇的是,从古罗马、中世纪前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至近代,各个时代的痕迹纠结辗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个时期的遗迹累积错落有致。
徜徉在欧洲心脏年会上,其实也是这种感觉。有的会场在阳光下,头上只有部分遮阳篷,听众可以选择坐在变形沙发上,晒着太阳听。有的会场就是在大会场中间竖起一个圆筒状幕布。在中间,还有一个圆筒状的幕布,下方则悬吊着面向三个方向的屏幕,投射着讲者的幻灯。从下往上的光影,投射在幕布上,呈现出炫目的色彩。
欧洲“整合”vs美国“改变”
就像罗马的遗迹,ESC会议也体现了其传统的包容。会议上的英语口音来自五湖四海,让人似懂非懂。不同国家的人似乎喜欢的话题“千奇百怪”:丹麦人在讲埋藏式心脏复律除颤器(ICD)置植入后车祸发生率是否增加了;英国人在讲心衰植入ICD或心脏再同步化治疗后远程监测到底有没有效;荷兰人在讲教育和行为干预对于心脏康复项目有没有用;法国人在反思全国在公共场合设置自动体外除颤器的得与失,澳大利亚人在谈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意大利人在谈地中海饮食……
这些全都不是美国人喜欢的“菜”。在会前,来自美国的几个医学专业媒体几次追问大会主席和学术委员会主席,ESC年会上到底有哪些进展可以改变临床实践?
这两个主席都有些支支吾吾地说:“有个叫DANISH的研究可能会改变临床实践。”这个研究将在非冠心病患者中使用ICD,有可能会改变临床实践。美国记者喋喋不休,问要是试验是阴性的呢?Pinto立马不说话了。
学术委员会主席“突然”想到,这次大会的主题不是“心脏团队(Heart Team)”吗?推广这个概念不就是改变临床实践吗?这是多么好的回答啊!美国记者终于不再追问了。
把心脏团队当作大会主题,真是绝妙的主意。不知道是谁想起来的。心脏团队是指在心脏病诊治时的多学科协作模式,其实也是美国人先提出来的,但也就是欧洲能把类似概念当作大会主题。欧洲人还把“环境与健康”和“心脏与系统器官的交互作用”当成大会主题。美国的会议主题一般离不开“转变”,比如2015年ACC的主题是“心血管护理的转变——从发现到救助”。
作为科学家、艺术家与工程师的达·芬奇
达·芬奇之于意大利,就像莎士比亚之于英国。在ESC大会上,怎么能少了达芬奇?这次让达·芬奇出场的是剑桥大学Francis Wells教授,他在大会开幕式上以“心脏与艺术”为题介绍了达芬奇对医学的贡献。
大会组委会邀请Wells估计是因为他出版了《达芬奇看心脏》(The Heart of Leonardo)一书。
达·芬奇观察到,心脏在几何意义上是一个复杂的锥形,运动是旋转的。它把自己扭曲,像拧毛巾一样拧干,但是心衰时,这种扭曲就会消失。
达·芬奇还发现心脏有四个腔,并画出了心脏瓣膜。他对心脏动脉瓣的研究领先了世界四百多年,还发现了心脏瓣膜开合的秘密。
早先人们认为,心脏有两个膜瓣,先开一个,关一个,一压,血就从这个心腔流进下一个心腔。达·芬奇有机械设计经验,他认为这不合理。瓣膜和纸相似,若以开关来算,用不了几年。还有的膜瓣是三瓣,有的是二瓣,主动开关的理论也不能解释。
达·芬奇用蜡灌满牛的心脏,蜡遇冷变硬,他用蜡与玻璃重新建立了心脏的结构,然后灌入混合草籽的水。随着悬浮的草籽在动脉根部的开口处旋转,他观察到小的漩涡。因此达芬奇推断,这些漩涡的作用是帮助关闭动脉瓣。膜瓣开合是被动的,依靠血流的湍流旋涡。流体流过管状孔的时候,中间的流速高,边缘的速度低。边缘的形成旋涡下压膜瓣,使之关闭。
1968年,达·芬奇的这一发现刊发在《自然》杂志上。两位牛津工程师发表的这篇文章只有一个参考文献,这个参考文献完成于五百年前,只有达芬奇的名字。近期的核磁共振成像则完全证实了达·芬奇的理论。
2007年,Wells根据达·芬奇的笔记,改良了心脏瓣膜手术,明显改善了瓣膜手术的疗效。Wells说,“科学家、艺术家跟工程师最好不要分家,而且应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和观察力。”
优良传统?
谈到艺术,罗马的艺术总体是实用主义,强调享乐、个性和宏伟壮丽。
罗马的标志性建筑首推举世闻名的大斗兽场就是典型。多少个世纪以来,这座于公元80年竣工的庞大建筑,象征着古罗马的荣耀与力量。ESC会标把斗兽场放到了图片中央,非常漂亮。大会的主会场布置也把大斗兽场的外形搬到了主会场。
意大利人有一个优良传统,那就是喜欢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东西,对于古迹真是敬若神明。这些古迹是历史的遗迹,其价值就在于唯一性和不可复制。
引以为傲的罗马大斗兽场,距今已有近2000年历史,公元72年,罗马皇帝韦帕芗强迫八万犹太和阿拉伯俘虏修建而成,能容纳观众约九万余人。在建筑史上堪称典范的杰作和奇迹。
现在的罗马人,陶醉于这座城市的陈旧,百年房屋自有古老的韵味。墙壁上斑驳的颜色,以及每一块花岗岩石砖,都能勾起许多落满灰尘的往事。于是一个个伟大的影像在心灵的屏幕上闪现。
激情与忘却
罗马并不是国家,而是一种激情,一种忘却。
今天,或许ESC大会的一些主题更有人文气息,让我们愿意来欧洲体验包容和多元的文化。但在美国能够改变临床实践的视角中,不得不说是一种嘲讽。
ESC大会上最重要的论坛是“热线(Hot line)”,包罗万象。美国心脏病学会议最重要的是“最新试验发布(Late-breaking trial)”,更多是临床随机、双盲对照研究,会议上其实听到更多的是质量改善,虽然感觉不近人情,是冷棒棒的现实,但却是命中要害。
欧洲的国家太多了,历史太长了,“改变”很不容易。美国心血管病医疗在变革方面则更多的动员了国家力量,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各种质量改善项目,进行质量评估,推行适宜性标准,建立国家的大数据平台,并与医保整合,这才有美国研究中动辄几十万、几百万的患者数据做支撑。
中国与欧洲和美国都不同,最近也把健康作为国家发展的重点。中国医生似乎更喜欢欧洲,欧洲更有人文和艺术精神,生活也更舒适;美国的生活则更辛苦一些。但美国相对欧洲而言,更加体现了体制创新,考虑的问题更多的是怎样从整体上从机制上提高水平。但中国其实还未起步,既要向欧洲学习,也要向美国学习。
有人说,罗马人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用刀箭棍棒令世人屈服,建立了一个宏大的罗马帝国;第二次是基督教的传播使罗马声名大噪,令世人称奇;第三次用法律规范世人的举止,举世皆闻罗马法。但与中国不同,罗马各个时期的遗迹累叠相安无事。
历史太长,有时也是负担。有人认为,由于罗马的历史太长久,遗迹太多,阻碍了发展。听说有一个“疯子”诗人,主张把罗马烧掉,否则意大利就不能发展。换句话说,费里尼的“对生命的激情”没有了,只剩下对生活的享受。
诗人多是疯子,疯子的话是不足为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