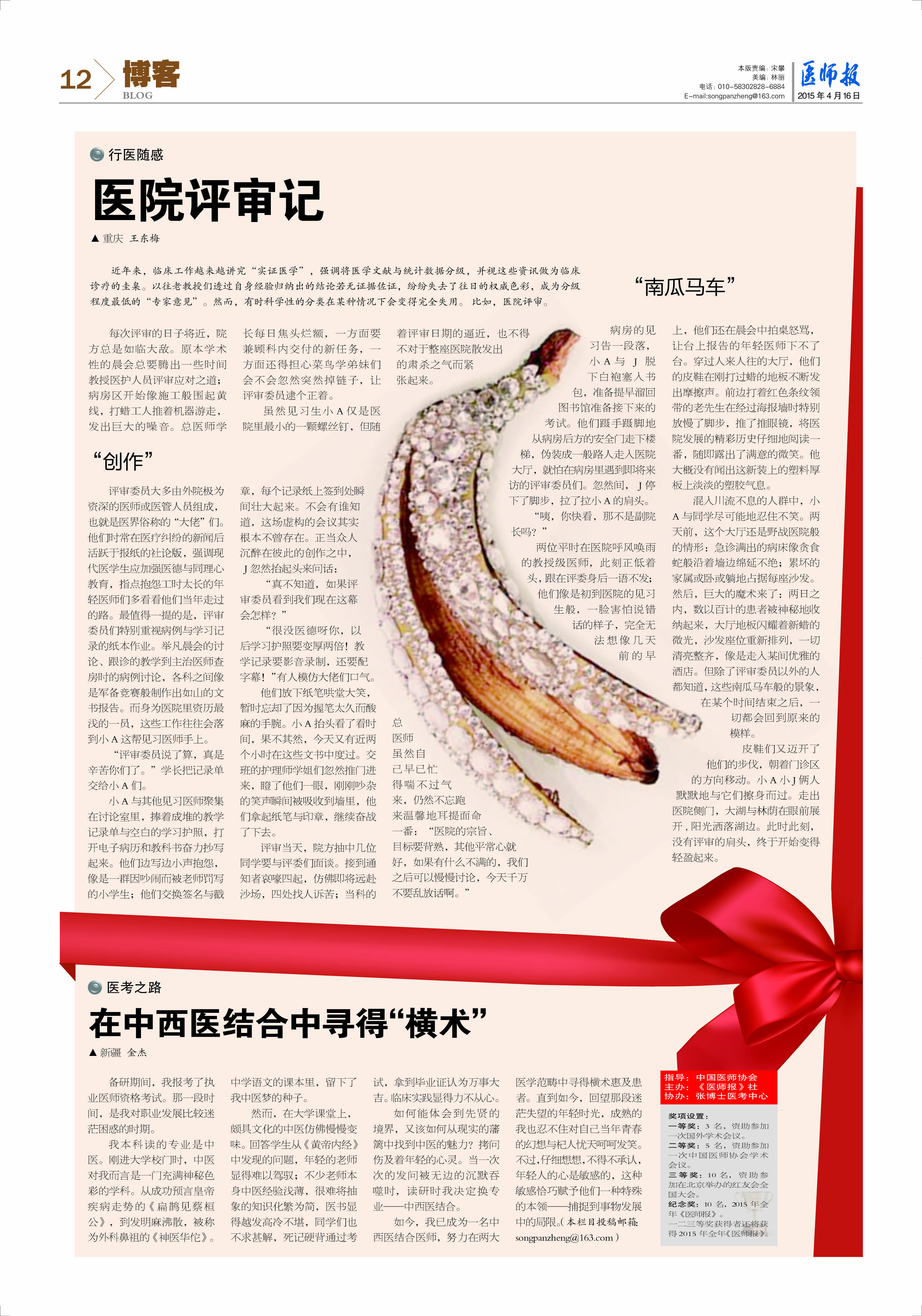近年来,临床工作越来越讲究“实证医学”,强调将医学文献与统计数据分级,并视这些资讯做为临床诊疗的圭臬。以往老教授们透过自身经验归纳出的结论若无证据佐证,纷纷失去了往日的权威色彩,成为分级程度最低的“专家意见”。然而,有时科学性的分类在某种情况下会变得完全失用。 比如,医院评审。
每次评审的日子将近,院方总是如临大敌。原本学术性的晨会总要腾出一些时间教授医护人员评审应对之道;病房区开始像施工般围起黄线,打蜡工人推着机器游走,发出巨大的噪音。总医师学长每日焦头烂额,一方面要兼顾科内交付的新任务,一方面还得担心菜鸟学弟妹们会不会忽然突然掉链子,让评审委员逮个正着。
虽然见习生小A仅是医院里最小的一颗螺丝钉,但随着评审日期的逼近,也不得不对于整座医院散发出的肃杀之气而紧张起来。
“创作”
评审委员大多由外院极为资深的医师或医管人员组成,也就是医界俗称的“大佬”们。他们时常在医疗纠纷的新闻后活跃于报纸的社论版,强调现代医学生应加强医德与同理心教育,指点抱怨工时太长的年轻医师们多看看他们当年走过的路。最值得一提的是,评审委员们特别重视病例与学习记录的纸本作业。举凡晨会的讨论、跟诊的教学到主治医师查房时的病例讨论,各科之间像是军备竞赛般制作出如山的文书报告。而身为医院里资历最浅的一员,这些工作往往会落到小A这帮见习医师手上。
“评审委员说了算,真是辛苦你们了。”学长把记录单交给小A们。
小A与其他见习医师聚集在讨论室里,捧着成堆的教学记录单与空白的学习护照,打开电子病历和教科书奋力抄写起来。他们边写边小声抱怨,像是一群因吵闹而被老师罚写的小学生;他们交换签名与戳章,每个记录纸上签到处瞬间壮大起来。不会有谁知道,这场虚构的会议其实根本不曾存在。正当众人沉醉在彼此的创作之中,J忽然抬起头来问话:
“真不知道,如果评审委员看到我们现在这幕会怎样?”
“很没医德呀你,以后学习护照要变厚两倍!教学记录要影音录制,还要配字幕!”有人模仿大佬们口气。
他们放下纸笔哄堂大笑,暂时忘却了因为握笔太久而酸麻的手腕。小A抬头看了看时间,果不其然,今天又有近两个小时在这些文书中度过。交班的护理师学姐们忽然推门进来,瞪了他们一眼,刚刚吵杂的笑声瞬间被吸收到墙里,他们拿起纸笔与印章,继续奋战了下去。
评审当天,院方抽中几位同学要与评委们面谈。接到通知者哀嚎四起,仿佛即将远赴沙场,四处找人诉苦;当科的总医师虽然自己早已忙得喘不过气来,仍然不忘跑来温馨地耳提面命一番:“医院的宗旨、目标要背熟,其他平常心就好,如果有什么不满的,我们之后可以慢慢讨论,今天千万不要乱放话啊。”
“南瓜马车”
病房的见习告一段落,小A与J脱下白袍塞入书包,准备提早溜回图书馆准备接下来的考试。他们蹑手蹑脚地从病房后方的安全门走下楼梯,伪装成一般路人走入医院大厅,就怕在病房里遇到即将来访的评审委员们。忽然间,J停下了脚步,拉了拉小A的肩头。
“咦,你快看,那不是副院长吗?”
两位平时在医院呼风唤雨的教授级医师,此刻正低着头,跟在评委身后一语不发;他们像是初到医院的见习生般,一脸害怕说错话的样子,完全无法想像几天前的早上,他们还在晨会中拍桌怒骂,让台上报告的年轻医师下不了台。穿过人来人往的大厅,他们的皮鞋在刚打过蜡的地板不断发出摩擦声。前边打着红色条纹领带的老先生在经过海报墙时特别放慢了脚步,推了推眼镜,将医院发展的精彩历史仔细地阅读一番,随即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他大概没有闻出这新装上的塑料厚板上淡淡的塑胶气息。
混入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小A与同学尽可能地忍住不笑。两天前,这个大厅还是野战医院般的情形:急诊满出的病床像贪食蛇般沿着墙边绵延不绝;累坏的家属或卧或躺地占据每座沙发。然后,巨大的魔术来了:两日之内,数以百计的患者被神秘地收纳起来,大厅地板闪耀着新蜡的微光,沙发座位重新排列,一切清亮整齐,像是走入某间优雅的酒店。但除了评审委员以外的人都知道,这些南瓜马车般的景象,在某个时间结束之后,一切都会回到原来的模样。
皮鞋们又迈开了他们的步伐,朝着门诊区的方向移动。小A小J俩人默默地与它们擦身而过。走出医院侧门,大湖与林荫在眼前展开,阳光洒落湖边。此时此刻,没有评审的肩头,终于开始变得轻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