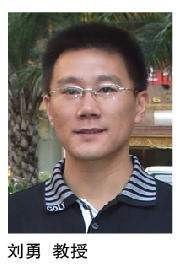
吗啡被“污名”久矣!谈起吗啡,人们往往会联想到毒品,很少人记得吗啡在历史和当下发挥的重要作用,也不知吗啡是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基本用药。
事实上,人类发现、种植、使用吗啡的来源物——鸦片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之久。早在5000年前,苏美尔人发现罂粟果实具有镇痛和迷幻的效果,于是从其浆果汁液中提炼出鸦片(音译为“阿片”),用作麻醉剂。约3000多年前,古巴比伦的人们已开始大面积地种植罂粟,称其为“快乐植物”。公元前二世纪,古希腊名医盖仑曾记录鸦片可治疗很多疾病。在《圣经》与荷马的《奥德赛》里,鸦片则被描述为上帝也会使用的“忘忧药”。
大概在六朝时代,罂粟由西亚传入我国,但种植范围不大。自宋代以来,医学典籍中出现了许多关于鸦片药用价值的记载,认为其在治痢、镇咳、止痛等方面有突出的疗效,民间称之为“药中之王”。 在元代,对其副作用已有认识,元朝名医朱震亨指出“其止病之功虽急,杀人之剑,亦深戒之”。两次鸦片战争前后,滥用吸食鸦片所导致的孱弱国民形象在人们脑海中留下深深的烙印。以致如今,人们提起鸦片仍有一种本能的畏惧和排斥,这种感觉又莫名的传递到了吗啡名下,最终构建了对吗啡具有原罪性质的“污名化”心理认知。
阿片中大概含有25种生物碱,吗啡是其中的一种。1806年德国著名的药剂师泽尔蒂纳第一次分离出了纯吗啡——一种有淡淡苦味的无色或白色结晶或粉末,因其具有明显的镇静催眠效果,泽尔蒂纳用希腊神话中的梦神墨菲斯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新发现的药物,其翻译的谐音即为“吗啡” 。
吗啡有强烈的麻醉镇痛作用,对绝大多数疼痛都有一定的止痛效果,其镇痛作用任何一种药物都无法比拟。据统计,人群在不加特殊管控的情况下,吗啡成瘾发生率约为3~6/10000人。如对吗啡的使用加以管控和规范,其成瘾的发生率则更低。由于吗啡的良好疗效和安全性,其在临终关怀患者的止痛中也得到广泛使用。我国对吗啡的使用有一套十分严格的医学监护制度,近20年来几乎没有关于医源性吗啡成瘾的报告。在西方医学界和我国台湾、香港地区,针对终末期患者的治疗,吗啡被称为“上帝送给人类的宝贝”之一。吗啡不仅具有镇痛作用,还能缓解呼吸困难,尤其是临终前的难治性呼吸窘迫感。正是由于吗啡的广泛使用,使许多临终和濒死患者明显减轻了因“喘不上气”而造成的痛苦。
基于以上药理学特点,世界卫生组织姑息治疗基本药物目录和国际临终关怀与姑息治疗学会(IAHPC)基本药物目录中,均把吗啡列为治疗疼痛和呼吸困难的基本药物。尽管我国还没有推出专门的姑息治疗基本药物目录,但已将吗啡列入国家的基本药物目录,成为镇痛基本用药。美国著名的MD安德森癌症中心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回顾分析了全美临终关怀医院中最常用的六种药物,吗啡高居第二位。韩国一项调查显示,临终关怀患者中使用量最大的药物是芬太尼(另一种阿片类药物)和吗啡。
由此可见,规范使用吗啡会给患者带来极大的临床获益。正如英文中“Drug”一词既是药品又是毒品一样,充满了辩证光芒,吗啡亦然!事实上,没有安全的药,只有安全的用药。作为一个帮助人类度过疾患困扰的良药,去其污名,还吗啡本来面目,正逢其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