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陈可冀院士在血瘀证与活血化瘀方面的研究,开创了新的理论体系,其影响不仅辐射全国,甚至被东北亚、东南亚地区同行所接受,被认为是我国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一个典范。其主持的“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获得2003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是我国中医药界第一项获得的最高科技奖项。
而陈可冀院士对“活血化瘀”的兴趣则是从阜外医院开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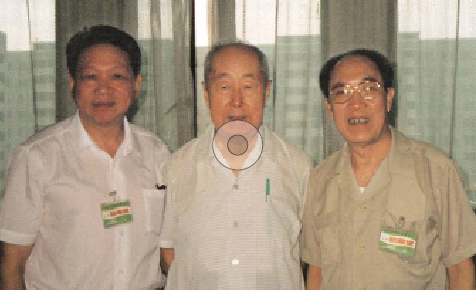
1993年,陈可冀院士(左)与吴英恺院士(中)、吴孟超院士(右)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大会上

1980年,陈可冀与阜外的师长和朋友在南京玄武湖畔。前左起翁心植、陈新、顾复生、戴玉华,后左起陈尚恭、陈可冀、吴英恺、胡旭东、孙瑞龙
遇见黄宛
陈可冀说,黄宛是他学习和进入心脏病学领域的启蒙老师。
1959年及1964年,陈可冀两次参加阜外医院主办的心电图学及心脏内科医师进修班。而1959年的心电图学进修课程完全是由黄宛教授和方圻教授两人每天轮流主讲,为时月余。
陈可冀还记得,那时黄宛教授才40岁,方圻教授比他小一岁。黄宛教授很严肃,陈可冀甚至还有些害怕他。第一次踏进他的办公室,黄宛教授问:你是哪里毕业的?陈可冀说是福建医学院(现福建医科大学)。
黄宛教授又问:“认识王中方教授吗?”
“认识,他是我们的内科主任。”陈可冀回答说。
原来,黄宛教授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当实习医生时,王中方教授是住院医师,正好是黄宛教授的老师,这样一聊,陈可冀与黄宛教授的关系就近了一些。
陈可冀回忆,黄宛教授非常严格,每周临床查房时,并不让医生们看着病历汇报患者病情,他所问的问题,都要求医生能记住数据和背诵回答。
1959年在心电图班进修时,没有多媒体或幻灯片等先进教学条件,黄宛教授和方圻教授拿着1米多长的木制“两脚规”在黑板上比划测量心电图的各项数据,以便大家理解,讲课十分生动精彩,给陈可冀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是进门阶梯。
1964~1965年,陈可冀脱产整整一年,在阜外医院心内科医师进修班学习。
按照阜外医院住院医师培训制度,必须24小时“住”在那时病房的五楼,夜间随时听候患者召唤,每天一大早起来在查房前自行抽血做完有关患者出凝血时间等项目的预备工作;并先后轮转到临床各专科及其他医技科室学习。这些培训极大地增进了陈可冀对心血管病学的知识,为他日后开展心血管疾病相关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本功。
弦脉研究
1959年,在黄宛教授及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张锡钧教授的指导下,陈可冀进行高血压病弦脉及其机制的研究,将不同弦脉记录图形分为三级。
为了探讨高血压病弦脉的产生机制,8名健康的志愿者分别在自己身上静脉点滴去甲肾上腺素做试验,其中包括陈可冀自己,根据张锡钧院士的建议,用von Euler萤光法测定。结果发现去甲上腺素含量增加的不同级别,或身体对该物质敏感度的增加,是形成弦脉的主要机理之一。
《高血压病弦脉及其机制的研究》这篇文章后来经黄宛教授亲自修改,发表在《中华内科杂志》1962年第10期上。陈可冀回忆,那时黄宛教授很重视,还专门把他叫到办公室给予指导,并介绍一本Wiggers CJ著的《Physiology in Health and Disease》作为参考。至今,陈可冀仍然感激于心。
29岁与黄宛同台报告
20世纪60年代前后,陈可冀和同事们在赵锡武教授、郭士魁研究员和黄宛教授的指导下,对262例高血压病例分为八种类型进行辨证论治。
当时世界卫生组织对高血压病是按血压水平、靶器官损伤程度以及病因学三种方式进行分期、分型及评定疗效,陈可冀提出,高血压病的治疗目的并非只是单纯的降压、降低心血管并发症的发生,还应包括“改善机体各系统的功能水平,以及适应社会环境能力等的生存质量”。
这个结果写成论文后,1959年在西安召开的全国心脏血管疾病学术会议上,受吴英恺院士的鼓励,陈可冀做了大会报告,同一天上午的报告还有邝安堃教授的高血压非药物治疗、黄宛教授的动脉粥样硬化研究进展的报告。当时陈可冀年仅29岁。
走上中西医结合循证研究之路
陈可冀在阜外进修学习的过程中,接触了大量冠心病心绞痛患者,有的患者每周要含用一瓶(100片)硝酸甘油来缓解疼痛,但应用活血化瘀方药后,可以减少用量。
联想到中医药传统理论认为“气血流通,百病自已”、“不通则痛、通则不痛”的观点,以及现代医学有关改善心肌供血思路之间具有相通性,陈可冀认为这是中西医结合较为容易沟通的切入点。
1961年,陈可冀根据临床所见,发表论文,指出活血化瘀疗法的经典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为此,阜外医院院长吴英恺院长还安排陈可冀在阜外医院讲堂做专题讲座。
1971~1972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北京地区成立了防治冠心病协作组,以阜外医院院长吴英恺院士为组长,10多家医院参与协作,选定以活血化瘀复方冠心2号为主要研究方剂。这项集体研究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为防治冠心病提供了活血化瘀思路与方向,辐射全国,形成了所谓“活血化瘀现象”。
后来陈可冀与富有经验的陈在嘉、寇文镕教授等合作研究,又改制成“精制冠心片”。在陶寿淇教授的支持下,与阜外医院、同仁医院及西苑医院等几家医院合作,采用随机双盲安慰剂交叉对照临床试验,进一步确认了其疗效,减少了服用量,多年来为《中国药典》收录。
陈可冀、郭士魁与黄宛、陈在嘉教授等联名将上述结果发表在1982年2月《中华心血管病杂志》上,这篇名为《精制冠心片双盲法治疗治疗冠心病心绞痛112例疗效分析》的文章,至今被我国循证医学界公认为是我国心血管病中西医结合领域第一篇符合循证医学要求的临床论著。
从此,更加坚定了陈可冀对活血化瘀的临床研究方向。“现在我们还在继续做这个工作。一个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也不容易。”陈可冀说。
与“家人”在一起
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在国务院及原卫生部的领导和组织下,全国掀起过西医学中医热潮。陈可冀回忆,刘力生、张之南、雷海鹏、朱预、刘干中、佘铭鹏、葛秦生、史济昭等,都曾参加过高级西医学习中医班,系统学习过中医药学。“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他们后来没有继续朝着这个方向研究。如果他们能坚持中西医结合之路,一定能做出比我们更多更大的成绩。”陈可冀不无感慨地说。
“阜外就像我的第二母校,使我在现代心血管病学知识水平上有较大的长进,且在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防治研究方面有了一定的拓展。”
至今,陈可冀仍然记得,1991年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友谊宾馆开会,刚刚被选进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的他第一次参加会议,一进大门,与吴英恺院士在会议室门口迎面碰着,吴英恺院士拉着他的手说:“可冀,过五关斩六将啊!”这句话给了陈可冀很大的鼓励,让他倍加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荣誉,也激励着他坚持中西医结合道路,破浪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