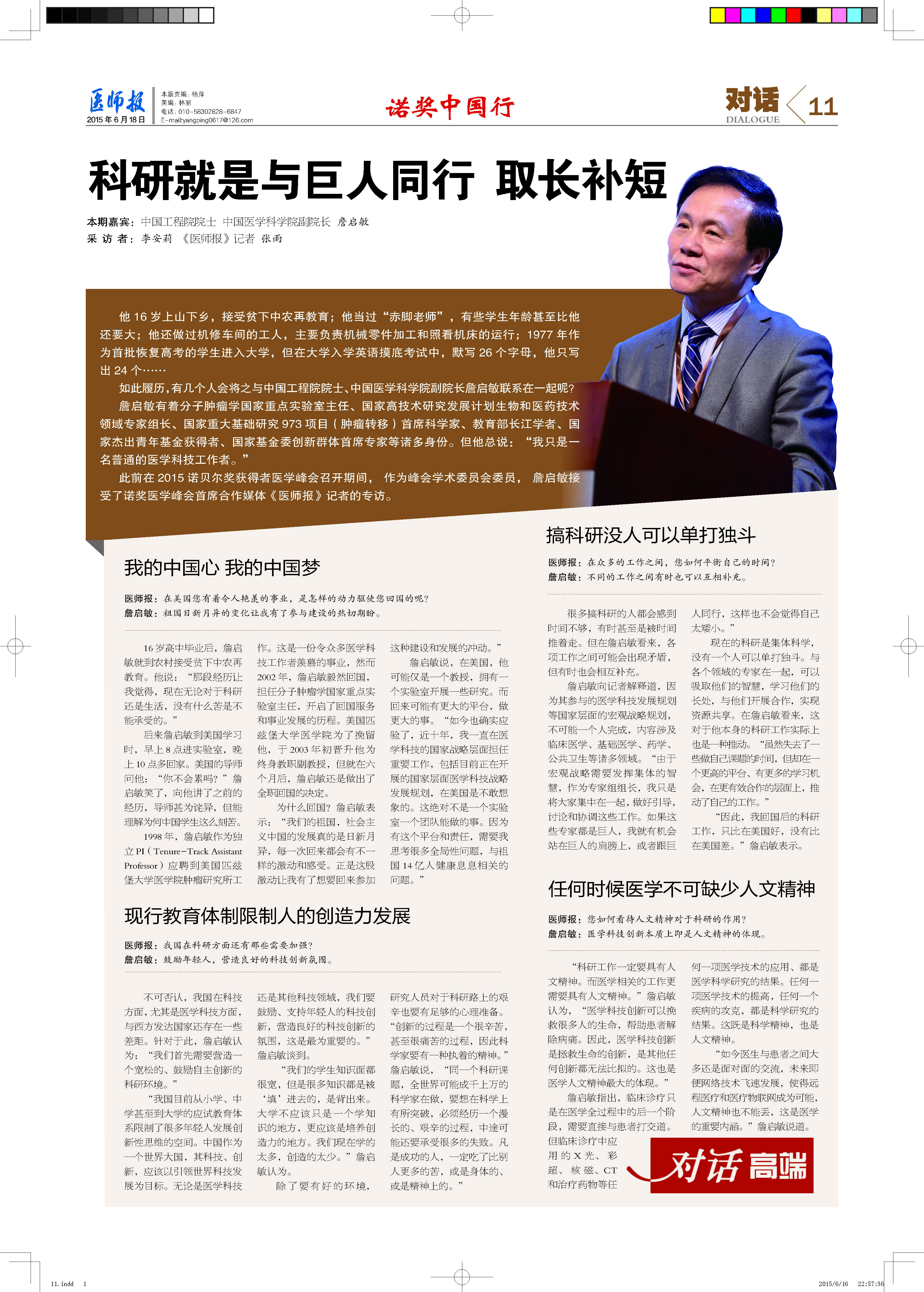他16岁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当过“赤脚老师”,有些学生年龄甚至比他还要大;他还做过机修车间的工人,主要负责机械零件加工和照看机床的运行;1977年作为首批恢复高考的学生进入大学,但在大学入学英语摸底考试中,默写26个字母,他只写出24个……
如此履历,有几个人会将之与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詹启敏联系在一起呢?
詹启敏有着分子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生物和医药技术领域专家组长、国家重大基础研究973项目(肿瘤转移)首席科学家、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国家基金委创新群体首席专家等诸多身份。但他总说:“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医学科技工作者。”
此前在2015诺贝尔奖获得者医学峰会召开期间, 作为峰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詹启敏接受了诺奖医学峰会首席合作媒体《医师报》记者的专访。

我的中国心 我的中国梦
医师报:在美国您有着令人艳羡的事业,是怎样的动力驱使您回国的呢?
詹启敏: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让我有了参与建设的热切期盼。
16岁高中毕业后,詹启敏就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说:“那段经历让我觉得,现在无论对于科研还是生活,没有什么苦是不能承受的。”
后来詹启敏到美国学习时,早上8点进实验室,晚上10点多回家。美国的导师问他:“你不会累吗?”詹启敏笑了,向他讲了之前的经历,导师甚为诧异,但能理解为何中国学生这么刻苦。
1998年,詹启敏作为独立PI(Tenure-Track Assistant Professor)应聘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肿瘤研究所工作。这是一份令众多医学科技工作者羡慕的事业,然而2002年,詹启敏毅然回国,担任分子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开启了回国服务和事业发展的历程。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为了挽留他,于2003年初晋升他为终身教职副教授,但就在六个月后,詹启敏还是做出了全职回国的决定。
为什么回国?詹启敏表示:“我们的祖国,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真的是日新月异,每一次回来都会有不一样的激动和感受。正是这股激动让我有了想要回来参加这种建设和发展的冲动。”
詹启敏说,在美国,他可能仅是一个教授,拥有一个实验室开展一些研究。而回来可能有更大的平台,做更大的事。“如今也确实应验了,近十年,我一直在医学科技的国家战略层面担任重要工作,包括目前正在开展的国家层面医学科技战略发展规划,在美国是不敢想象的。这绝对不是一个实验室一个团队能做的事。因为有这个平台和责任,需要我思考很多全局性问题,与祖国14亿人健康息息相关的问题。”
现行教育体制限制人的创造力发展
医师报:我国在科研方面还有那些需要加强?
詹启敏:鼓励年轻人,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氛围。
不可否认,我国在科技方面,尤其是医学科技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还存在一些差距。针对于此,詹启敏认为:“我们首先需要营造一个宽松的、鼓励自主创新的科研环境。”
“我国目前从小学、中学甚至到大学的应试教育体系限制了很多年轻人发展创新性思维的空间。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其科技、创新,应该以引领世界科技发展为目标。无论是医学科技还是其他科技领域,我们要鼓励、支持年轻人的科技创新,营造良好的科技创新的氛围,这是最为重要的。”詹启敏谈到。
“我们的学生知识面都很宽,但是很多知识都是被‘填’进去的,是背出来。大学不应该只是一个学知识的地方,更应该是培养创造力的地方。我们现在学的太多,创造的太少。”詹启敏认为。
除了要有好的环境,研究人员对于科研路上的艰辛也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创新的过程是一个很辛苦,甚至很痛苦的过程,因此科学家要有一种执着的精神。” 詹启敏说,“同一个科研课题,全世界可能成千上万的科学家在做,要想在科学上有所突破,必须经历一个漫长的、艰辛的过程,中途可能还要承受很多的失败。凡是成功的人,一定吃了比别人更多的苦,或是身体的、或是精神上的。”
搞科研没人可以单打独斗
医师报:在众多的工作之间,您如何平衡自己的时间?
詹启敏:不同的工作之间有时也可以互相补充。
很多搞科研的人都会感到时间不够,有时甚至是被时间推着走。但在詹启敏看来,各项工作之间可能会出现矛盾,但有时也会相互补充。
詹启敏向记者解释道,因为其参与的医学科技发展规划等国家层面的宏观战略规划,不可能一个人完成,内容涉及临床医学、基础医学、药学、公共卫生等诸多领域。“由于宏观战略需要发挥集体的智慧,作为专家组组长,我只是将大家集中在一起,做好引导,讨论和协调这些工作。如果这些专家都是巨人,我就有机会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或者跟巨人同行,这样也不会觉得自己太矮小。”
现在的科研是集体科学,没有一个人可以单打独斗。与各个领域的专家在一起,可以吸取他们的智慧,学习他们的长处,与他们开展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在詹启敏看来,这对于他本身的科研工作实际上也是一种推动。“虽然失去了一些做自己课题的时间,但却在一个更高的平台、有更多的学习机会,在更有效合作的层面上,推动了自己的工作。”
“因此,我回国后的科研工作,只比在美国好,没有比在美国差。”詹启敏表示。
任何时候医学不可缺少人文精神
医师报:您如何看待人文精神对于科研的作用?
詹启敏:医学科技创新本质上即是人文精神的体现。
“科研工作一定要具有人文精神。而医学相关的工作更需要具有人文精神。”詹启敏认为,“医学科技创新可以挽救很多人的生命,帮助患者解除病痛。因此,医学科技创新是拯救生命的创新,是其他任何创新都无法比拟的。这也是医学人文精神最大的体现。”
詹启敏指出,临床诊疗只是在医学全过程中的后一个阶段,需要直接与患者打交道。但临床诊疗中应用的X光、彩超、核磁、CT和治疗药物等任何一项医学技术的应用、都是医学科学研究的结果。任何一项医学技术的提高,任何一个疾病的攻克,都是科学研究的结果。这既是科学精神,也是人文精神。
“如今医生与患者之间大多还是面对面的交流,未来即便网络技术飞速发展,使得远程医疗和医疗物联网成为可能,人文精神也不能丢,这是医学的重要内涵。”詹启敏说道。